-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普林茲文學獎銀牌獎、美國圖書館協會青少年最佳讀物、美國青少兒圖書協會國際傑出圖書榮譽選書!
★英美法澳12項文學獎、6度入選榮譽選書,全球盛讚,持續熱烈迴響中!
★Mr.V|FB粉絲團「Novel小說」版主
NeKo嗚喵|Youtuber/說書人
冬陽|小說愛讀人
余小芳|推理文學愛好者
李泳泉|誠品信義書店門市組長
凌性傑|知名作家
郝譽翔|知名作家
許愷育|都會生活台鋁採購
陳心怡|紀錄片導演、知名作家
陳綱儀|金石堂網路書店文學小說線
銀色快手|知名作家
劉盈萱|金石堂網路書店文學PM 盛讚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令人不安卻又卻觸動人心!
從膽戰心驚到熱淚盈眶,一個不同凡響的綁架故事!
駭人聽聞的綁架事件、令人窒息的囚禁關係、令人動容的真摯情感,
被綁架的女孩道出在野性大地度過的奇異歲月……
十六歲的潔瑪原本過著再平凡不過的人生,和朋友一起做些青少年風格的蠢事、偶爾和父母意見不合大吵大鬧,這一切卻在喝一杯咖啡的時間內徹底改變。
潔瑪和家人在曼谷機場轉機時,被一位名叫泰伊的神秘青年綁架了。泰伊並不像典型的綁架犯,他年輕、身材結實、而且非常迷人,心中似乎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
潔瑪被帶離熟悉的一切,來到與世隔絕的澳洲內陸,進入沙漠、高溫、塵土、以及危險之中,而綁架犯竟然還希望潔瑪能愛上他。
在澳洲炙熱豔陽之下、一片荒蕪的沙漠中央,潔瑪該如何逃脫被綁架的夢魘、泰伊又該如何讓她明白自己的一片真心?
事情在那時候就變了。我變得很慢,我四周的一切則在加速。很不可思議,那麼少的一點粉末卻能帶出這麼大的效果。
「你覺得怎麼樣?」你問。
你看著我;你的眼睛睜得很大。我張開嘴,想告訴你我沒事,但聽不懂自己說了什麼。那只是一連串的噪音;我的舌頭麻木地說不出話。我記得燈光變成了一片耀眼的火焰。我記得冷氣讓我的手臂發冷。咖啡的氣味和尤加利葉的味道混在一起。你的手緊抓著我的手臂,把我拉走,把我偷走。
當我跌跌撞撞地站起來時,我一定是不小心打翻你的咖啡杯了。稍後,我在腿上看見一個燙傷的痕跡,一片粉紅色的傷痕在我的左膝上擴散。現在它有一點發皺,像是象皮。
你帶我走得很快。我以為你是要帶我回去我的飛機那裡,帶我回去我父母所在的登機口。那段路很長,比我記得的還長得多。當你拉著我走過自動人行道時,我覺得我們像是在飛一樣。你和穿著制服的人們說話,把我拉向你,好像我是你的女朋友。我對他們點頭微笑。你拉著我走上階梯。一開始,我的膝蓋彎不下去,而那讓我忍不住格格笑起來。接著我的膝蓋便軟得像棉花糖做的。新鮮的空氣迎面撲來,聞起來帶著花香、煙味與酒氣。有人在某處輕聲說著話,大笑聲聽起來像猴子的尖叫。你拉著我走過一處灌木叢,接著走過一棟建築物的轉角。一根樹枝卡在我的頭髮裡。我們在垃圾箱附近。我能聞到腐爛水果的氣味。
你再度把我拉向你,抬起我的臉說了些什麼。你的一切都顯得參差其,漂浮在垃圾箱四周的氣體上。你美麗的嘴唇像毛毛蟲般蠕動。你的體溫從我的指尖直竄上手臂。你又說了點什麼。我點點頭。某部分的我是聽得懂的。我開始褪去衣物。我靠著你脫下牛仔褲。你給了我新的衣服。一條長裙。一雙高跟鞋。然後你轉過身。
我一定把衣服穿上了。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做到的。接著你脫去上衣。在你穿上另一件襯衫時,我伸出手,摸了摸你的背。溫暖而紮實,像樹幹一樣的棕色。我不知道我在想什麼,甚至不知道我有沒有在思考,但我記得自己覺得必須碰觸你。我記得你皮膚的觸感。很奇怪,我對觸感的記憶比對想法的印象更深。但我的手指仍因那個碰觸而發麻。
你又做了一些別的事,在我頭上戴上一個粗糙的東西,並用某個黑漆漆的物品遮住我的眼睛。我緩緩地移動。我的腦子跟不上這一切。某樣東西落入垃圾箱裡,發出一聲悶響。我的嘴唇上出現了某種滑膩的東西。是口紅。你給了我一塊巧克力。濃郁。苦澀。柔軟。中心包著液體。
接下來的事情讓我更困惑。當我向下看去,我看不見自己的雙腳。我們再度開始行走時,我覺得自己好像是用腿的斷樁在走。我開始慌了,但你一手攬住我。溫暖而堅固⋯⋯安全。我閉上眼睛,試著思考。我不記得我把自己的包放在哪裡了。我不記得任何事情。
我們被人群包圍。你把我推入一片模糊的面孔與顏色之間。你肯定把一切都計畫好了;機票、新護照、我們前進的路線、通過安檢的方法。這是計畫最周全的偷竊,還是只是好運?要把我帶回曼谷機場、登上另一架不同的飛機,還不被任何人發現、不被我發現,這不應該這麼容易的。
你不斷餵我吃巧克力。那股濃郁而苦澀的味道⋯⋯不斷迴盪在我的嘴裡,附在我的牙齒上。在你出現之前,我很愛巧克力。現在就連它的氣味都令我作嘔。第三顆巧克力之後,我就昏了過去。我坐在某處,靠在你身上。我很冷,而我需要你的體溫。你對著別人說了點什麼來解釋我的狀況。
「喝太多了。」你說。「我們正在慶祝。」
接著我們擠進一間廁所裡。當我身下的馬桶把內容物沖走時,我感覺到空氣的流動。
接著我們又開始走了。或許是另一座機場。四周是更多的人⋯⋯空氣中充滿了花香,甜蜜、清新、帶著熱帶氣息;好像剛下完雨的樣子。四周很黑。是晚上。但並不冷。當你拉著我走過一個停車場時,我開始轉醒。我開始反抗。我試著尖叫,但你把我拉到一輛卡車後方,並用一塊布蒙著我的嘴。世界又變得一片模糊。我往你身上倒去。在那之後,我只記得在一輛搖晃的車裡驚醒。引擎永無止境地抗議著。
但我的確記得醒來的那段時間。還有熱度。它刨抓著我的喉頭,試著阻止我呼吸。這讓我再度快要昏迷。接著出現的是疼痛⋯⋯反胃。
***
至少你沒有把我綁在床上。就這一點而言,我很感激。電影裡的受害者總是被綁在床上。但我還是不太能動。每次我只要轉動身子,嘔吐感就湧上喉頭,頭暈目眩。我身上蓋個一張薄被單。我覺得自己像是躺在一片火海之中。我睜開眼睛。一切都在扭動旋轉,顏色模糊。我在一個房間裡。牆壁是木頭做的:長長的木板,角落用釘子釘著。光線刺痛著我的雙眼。我看不見你。我小心翼翼地轉頭張望。我在嘴裡嚐到嘔吐物的味道。我將它嚥下。我的喉嚨很緊繃。聲音沙啞。毫無用處。
我再度閉上眼睛。我試著深呼吸。我在腦中點名身體各個部位。我的手臂還在,腿和腳也是。我動了動手指。全都還能動。我摸了摸腹部。我身上穿著一件T恤,內衣則卡進胸口的皮膚裡。我光著腿,牛仔褲不見了。我摸了摸身邊的床單,接著把手放在大腿上。我的皮膚開始發燙,並幾乎立刻變得黏膩。我的手錶也不在手腕上。
我的手滑過內褲,感覺著布料下方的身體。我不知道我期望自己會摸到什麼。或許是血。破碎的肉體。疼痛。但什麼都沒有。你把我的內褲脫下了嗎?你進入過我了嗎?如果有的話,你為什麼又幫我把內褲穿回來呢?
「我沒有強暴你。」
我抓住床單,轉過頭。我試著找你。我的雙眼仍然看不清楚。我聽得出來,你在我後面。我試著把自己推到床邊,好遠離你,但我的手臂不夠有力。它們搖晃著,接著讓我摔進床單裡。血液在我體內流竄。我幾可以聽見我的身體開始流動,開始復甦。我試著發出聲音,發出一聲哀號。我的嘴抵著枕頭。我聽見你在某處踏出一步。
「你的衣服在床邊。」
你的聲音讓我顫抖。你在哪裡?你有多近?我微微睜開眼睛。這動作並沒有很痛。床邊的木椅上,整齊地放著一條折好的新牛仔褲。我的大衣不在那裡。我的鞋也不在。椅子下放著一雙咖啡色的皮靴。穿著鞋帶,質感很好。不是我的。
我可以聽見你的腳步聲朝我走來。我試著捲起身子躲開。一切都感覺好重。好慢。但我的腦子可以運作,我的心跳在加速。我在一個可怕的地方。這一點我還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到這裡的。我不知道你對我做了什麼。
我聽見地面又發出幾次吱嘎聲,並感覺到恐懼從胸口湧上喉頭。一件淺棕色的卡其褲在我面前停下。我的雙眼高度正好在你的胯下與膝蓋之間,正對著上頭紅色的泥土痕跡。你什麼也沒說。我聽見自己的呼吸聲加快。我抓住床墊。我逼自己向上看去,視線直到你的面孔才停下。我的呼吸停了一秒。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半期待你會是另外一個人。我不希望這個站在床邊的人,就是我在機場覺得很有吸引力的人。但你就站在那裡;你的藍眼睛,你金黃色的頭髮,還有小小的疤痕。但你現在看起來並不美了。只是邪惡。
你面無表情。那雙藍眼睛看起來很冰冷。你的嘴唇很薄。我把被單盡可能拉高,只露出眼睛看著你。你站在那裡,等著我開口,等著我問問題。我什麼都沒問,但你還是回答了。
「是我把你帶來這裡的。」你說。「你會不舒服,是因為藥的關係。你這段時間都會覺得很怪⋯⋯呼吸困難、暈眩、反胃、出現幻覺⋯⋯」
你一邊說話,你的臉一邊旋轉。我閉上眼睛。我眼冒金星;一整片閃爍、旋轉的小星星。我聽見你朝我移動。越來越近。我試著開口。
「為什麼?」我低聲說。
「我必須這麼做。」
當你坐下時,床發出一聲吱嘎聲,我的身子抬起了一點。我把身體挪開。我試著把腿放到地上,但動不了。整個世界似乎在我身邊旋轉。我覺得我就要滑倒了。我轉開頭,並等著反胃的感覺再度出現。但沒有。我把腿收到胸前。我的胸口緊繃地哭不出來。
「我在哪裡?」
你頓了頓才回答。我聽見你吸了一口氣,然後嘆息。你換了個姿勢,衣服沙沙作響。此時我才發現,除了你的聲音之外,我什麼都聽不見。
「你在這裡。」你說。「你很安全。」
***
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這段時間一片模糊,像是某種扭曲的惡夢。我想你給了我食物和水。但你沒有幫我洗澡。這點我知道,因為當我醒來時,我身上散發著臭味。我渾身是汗,全身潮濕,T恤黏在身上。我需要上廁所。
我躺在那裡聽著。我拉直耳朵,想聽見什麼。但四周一片死寂。死寂得詭異。房裡甚至沒有你移動的吱嘎聲或沙沙聲。沒有遠處高速公路的低鳴。沒有火車的隆隆作響。什麼都沒有。只有這個房間。還有熱氣。
我試了試自己的身體。我抬起一條腿,接著是另外一隻,又動了動腳趾。這次我的四肢沒感覺這麼沈重了;我越來越清醒。我盡可能保持安靜,撐起身子,好好地打量房間一圈。你不在這裡。這裡只有我。我,還有我躺著的雙人床,床邊有張小床頭桌,一小櫃抽屜,還有放著牛仔褲的椅子。這裡的一切都是木頭做的,一切都很基本。牆上沒有畫或照片。我的左邊有一扇窗,窗簾厚重。外頭一片光亮。現在是白天。很熱。我面前有一扇關著的門。
我又等了一會,等著聽你的聲音。接著我掙扎地來到床邊。我覺得頭暈,好像我的身體就要摔倒,但我做到了。我抓住床墊的邊緣,並要我自己呼吸。我才發現我一直屏著氣。我小心翼翼地把一隻腳放到地上。接著是另一隻。我把重心放下去,抓著床頭桌穩住自己。我的視線暗了一下,但我站在那裡,閉上眼睛,聽著。還是什麼聲音也沒有。
我伸手拿過牛仔褲,坐回床上,穿上褲子。這條褲子又緊又厚,緊貼著我的雙腿。褲頭的釦子陷進我的膀胱,讓我更想上廁所了。我懶得穿靴子;光腳更安靜。我朝門口踏出一步。地板和其他的東西一樣是木頭做的,踩在腳下十分冰冷,木板之間的縫隙透出下方的黑暗空間。我的腿和木頭一樣僵硬。但我終於來到門邊。我壓下門把。
門的另外一側更陰暗。等我的眼睛適應光線後,我看見一條長長的走廊——又是木頭的——總共有五扇門,兩扇在左邊,兩扇在右邊,還有一扇在走廊的盡頭。所有的門都是關著的。我踏出第一步,地板發出微微的吱嘎聲。聲音讓我僵在原地。但門後沒有傳來任何聲音,不像任何人有聽見我的樣子,所以我又踏了另一步。哪一扇門才能帶我逃出去?
我走向右手邊的其中一扇門,抓住冰冷的金屬門把。我把門把向下壓,屏住呼吸,然後把門拉向自己。我停了下來。你不在裡面。那是一間黑暗的灰色房間,有個水槽和淋浴間。是一間浴室。浴室底端是另一扇門。或許是馬桶。有那麼一瞬間,我有點猶豫該不該冒險快速上個廁所。老天,我真的得尿尿。但我還會有多少像這樣的機會?或許就只有這一次。我退回走廊上。我可以尿褲子沒關係。或是去外面再上。但我需要離開這裡。如果我能逃出去,其他怎樣都沒關係。我會找到人幫我。我會找到地方去。
我還是聽不見你在哪裡。我伸手扶著牆,穩住自己,然後走向盡頭的門。一步,兩步。每一步都發出微微的吱嘎聲。我的手撫過木頭表面,木屑卡進手指裡。我的呼吸又快又響,像狗在喘氣,我的雙眼掃視著一切,試著理解我在哪裡。汗水從我的頭皮上滑下,流過脖子,流過我的背,流進牛仔褲裡。我的記憶只到曼谷機場。但我上了一架飛機,對吧?還有一輛車?或許這些都只是夢的一部分。我的父母呢?
我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個輕而小的腳步上。我想驚慌地尖叫。但我得保持冷靜,這點我還知道。如果我開始思考我在哪裡、還有發生了什麼事,我會嚇得無法移動。
盡頭的門很輕易就開了。另一側是一間大而昏暗的房間。我縮回走廊上,準備拔腿就跑。我的腸胃翻攪著,膀胱的壓力大得幾乎無法忍受。但房裡沒有任合動靜。沒有任何聲音。我快速掃視房間,你不在裡面。我可以看見一張沙發和三張木頭椅;全都是粗糙的製作,像臥房裡的其他傢俱一樣基本。牆上有個像壁爐的地方。牆壁是木頭做的。窗戶也被窗簾遮住了,讓一切覆上一層暗棕色的光澤。沒有任合裝飾。沒有任何照片。這個房間就和整間屋子的其他地方一樣光禿。這裡的空氣沈重而停滯,像塞滿棉花的大衣。
我的左邊有一個廚房,中央擺著一張桌子,四周全是櫥櫃。窗簾一樣是拉下來的,但盡頭有一扇門,上頭結霜的窗戶透出明亮的光線。外面。自由。我沿著牆走過去。膀胱傳來的疼痛加劇,牛仔褲實在太緊了。但我來到門邊。我碰了碰門把。我輕推了一下,半期待它是上鎖的。但它沒有。我驚訝地倒抽一口氣。接著我回過神來,把門拉向自己。我把門開到足以讓自己擠出去。我踏出屋子。
陽光立刻灑在我身上。一切都明亮得讓我心痛。而且很熱。比屋子裡還熱。我的嘴巴立刻就乾了。我掙扎著呼吸,靠在門口。我用手遮住眼睛上方,試著睜開眼。眼前的明亮讓我什麼也看不見。好像我踏進了死後的世界,只是這裡一個天使也沒有。
我逼自己睜開眼睛,看了看四周。一點動靜也沒有,你不在這裡。除了這間屋子之外,右邊還有兩棟建築物。它們看起來都像是臨時搭建的,是一片片金屬與木板所搭成。小屋旁邊的金屬遮棚下,有一輛破爛的四輪車和拖車。然後就是一片陸地。
我發出一聲嗚咽。我眼睛所見的地方,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片平坦的棕色大地,一路延伸到地平線。四周都是沙,還有更多的沙,只有少數幾叢灌木,還有幾棵沒有葉子的樹。土地一片死寂而乾涸。我在一片荒地上。
我轉過身。這裡沒有別的屋子。沒有道路。沒有人。沒有電話線或人行道。什麼都沒有。一片空盪。只有熱氣與地平線。我的指甲深深刺進手掌心,等著疼痛來告訴我,我不是在做夢。
在我邁開腳步時,我就知道沒有任何希望。我能跑去哪裡?到處看起來都一樣。我懂你為什麼不鎖門、為什麼沒有把我綁在床上了。外面這裡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任何人。只有我們。
我的腿僵硬而遲緩,大腿的肌肉立刻就痛了起來。我的光腳刺痛著。泛紅的土地看起來什麼也沒有,但地上有尖刺和石頭,帶刺的植物與細小的根。我咬著牙,半跑半跳地前進。但沙子很燙,就算這麼做還是很痛。
你當然看見我了。大約距離屋子一百米左右,我就聽見車子發動的聲音。我繼續跑,膀胱伴隨著每一個腳步脹痛著。我甚至加快了腳步。我盯著遠處地平線上的某處,然後往前跑。我的呼吸急促,雙腿沈重。我的腳在流血。我聽見輪胎捲起沙塵,朝我前來。
我試著蛇行,心想那或許會拖慢你的速度。我已經半瘋狂了,抽著氣、嗚咽著,大口呼吸。但你繼續前進,輪胎尖叫、引擎怒吼,快速朝我開來。我可以看見你轉動方向盤,把車子轉過來。
我停下腳步,換個方向。但你就像拿著繩索的牛仔,圍著我繞圈,一次次擋下我。你知道我很快就會體力不支,再也跑不動了。我就像隻發狂的牛般繼續跑著。我不斷從你身邊跑開,距離一次比一次短。我最終還是倒下了。
你停下車,引擎熄火。
「沒用的。」你喊道。「你不會找到任何東西或任何人的。」
我哭了起來,啜泣聲像是永無止境般從我體內發出。你打開車門,抓住我T恤的後頸。你把我拉向你,我的手拼命刨抓著地面。我轉頭咬了你的手。狠狠的一口。你咒罵一聲。我知道你流血了。我嚐到了血味。
我爬起來,繼續跑。但你很快地再度抓住我。這次你用全身的力氣將我壓制在地。沙子摩擦著我的嘴唇。你趴在我身上,胸口抵著我的背,腿抵住我的大腿上方。
「放棄吧,潔瑪。你難道看不出來,你根本無處可去嗎?」你對著我耳朵大吼。
我再度掙扎,但你更用力地壓著我,把我的手壓制在身側,緊抓著我。我嚐到泥土,你的身子重重地壓住我。
此時我再也憋不住尿了。
14.8*21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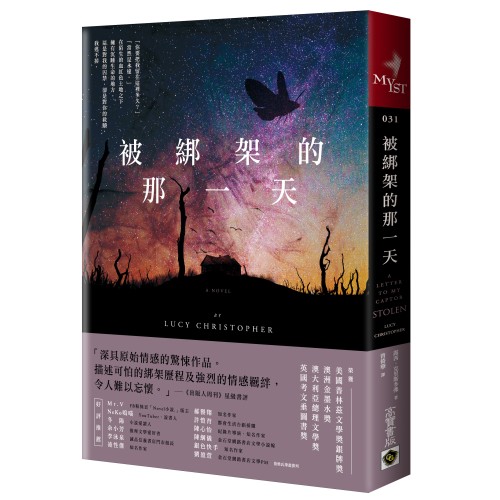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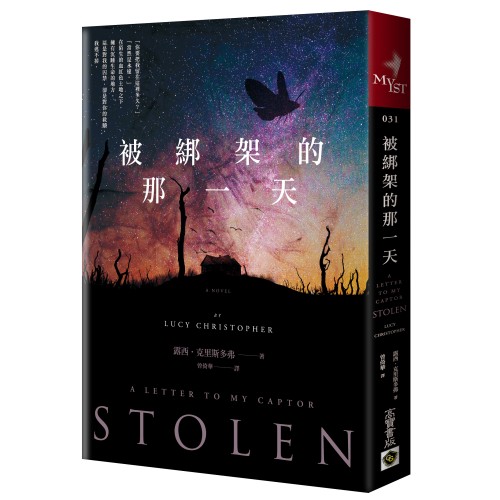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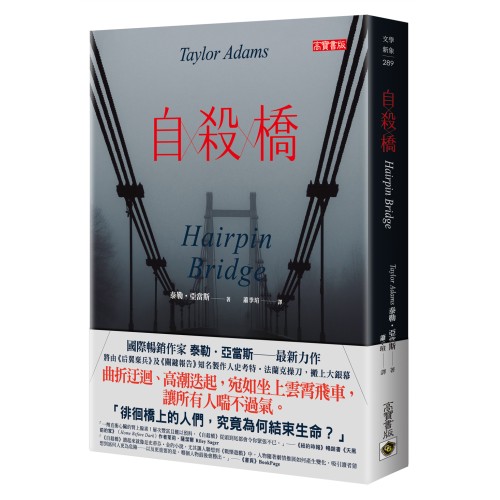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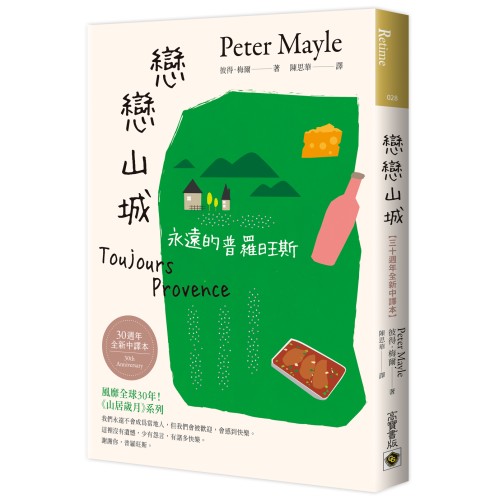
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