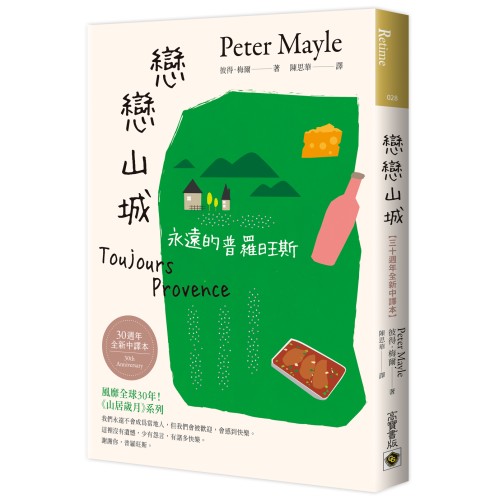-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藍色雷斯里
影評人膝關節
知名部落客喬齊安(Heero)
逆轉讀書會主辦人 栞
苦悶中年男
臥斧
快雪
旭日之丘
共同推薦
每張照片都有故事,有的很溫馨,有的很詭異。
最重要的是,這些照片,都是真的……
從小,雅各的爺爺為他說的床邊故事十分與眾不同,他會一遍又一遍地說著自己童年時的詭異故事:在英國威爾斯的孤兒院裡,院長是會變成大鳥的隼夫人,院童中有不用繩子綁住就會飄到空中的小女孩,後腦杓有第二張嘴的人,當然,還有一個透明的男孩。
小時候的雅各對爺爺的故事深信不疑,但隨著時間過去,長大的他認為那只是些重複曝光的舊照片,爺爺只是個想像力豐富的老人,畢竟,這世上怎麼會有飄在空中的小女孩呢?
但在那一天,他看到了。
雅各親眼看到爺爺故事中的「怪物」。
那一天,怪物在雅各面前襲擊爺爺、奪走他的生命。雅各開始明白,爺爺說的不是故事,是他真實經歷的一切。他也記得,在爺爺斷氣之前,抓著他的領子對他說:「去找大鳥、去圈套裡、去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他決定完成爺爺的遺願,前往威爾斯的怪奇孤兒院、尋找隼夫人。不管這是否代表怪物將會盯上他,把他當作下一個目標……
***
照片是祕密的祕密,
它告訴你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少。
――攝影師 黛安•艾巴斯
蘭森•瑞格斯在馬里蘭州的牧場長大,因為牧場實在無聊,所以閒來無事只能跟自己玩耍。小時候的他對於照片特別感興趣,很愛看圖編故事。後來雖然搬到了佛州這個熱鬧的城市,但也沒有好一點,在網路和電視台都不太發達的年代,他依舊很無聊。於是看圖編故事的習慣便一路持續。
數年前,他開始收集照片。因為知名攝影師的照片實在很貴,所以他把目標轉往跳蚤市場。在跳蚤市場裡,你可以找到蒙了灰的寶石,也可以找到別人用過的水壺、杯具等生活用品。然而,抓住他目光的卻是一張張泛黃、老舊的生活照。
最早,瑞格斯本來只打算集結蒐集的照片,個別編寫圖說、出版成冊。但他的天才編輯覺得,既然能幫每張照片編故事,怎麼不直接用這些照片寫成一個故事呢?
在編輯提出建議後,瑞格斯似乎也覺得有趣,於是就這麼做了。
把這些照片串連成故事並不容易,要獲得充足的、適合入故事的照片也不容易。所以,他開始尋找跟他一樣喜歡蒐集老照片的收藏家。在這些收藏家的幫助下,他終於完成了這本小說。在書後,瑞格斯亦一一列出照片的擁有者,一一致上感謝。
這些又黃又舊、殘破不堪的老照片散發出濃濃的故事氣息,它好像總是有話想說,你也忍不住猜測,在鏡頭的另一端是怎樣的光景:是誰照下了這些照片?照下相片時的天氣如何?這張照片後來收在誰的抽屜?又是為什麼來到了跳蚤市場?
奇妙的是,如果不論照片是黑白或老舊,有些照片其實是很平常的。然而,就因為多了歲月留下的斑駁、泛黃,照片便生出一種詭異陰森的氣味,這是一種因為時間流逝而產生的距離感,也是數位相片怎麼也無法記錄的光陰痕跡。
在看完這本小說後,也許你會有種想去翻看舊照片的衝動;又或者,會想要把數位照片洗出來,放在抽屜裡十年八年。說不定還可以為那照片寫下一個故事。
未來的事,誰知道呢?
§爺爺的相本§
正當我開始接受平凡無奇的生活時,不凡的事逐一發生了。這些突如其來的轉變令人錯愕,永遠改變了我,也把我的人生劃分為前後兩階段:「之前」和「之後」。之後一連串不凡的變化接踵而來,全都和我的祖父亞伯拉罕.波曼息息相關。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波曼爺爺是我所認識的人物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他待過孤兒院、打過仗、搭蒸汽船遠度重洋、騎馬橫越沙漠、參加過馬戲團表演,也經歷過荒野求生,他對槍枝和防身術了若指掌,除了英文之外,還會至少三種語言。對一個從未離開過佛羅里達州的孩子而言,他的人生充滿濃烈的異國色彩。每次只要我們聚首,我總是殷切哀求他告訴我更多故事;而他總是依順著我,輕聲訴說他的經歷,彷彿這一切是不可告人的祕密,而我是他唯一信任的人。
六歲的時候,我決定要成為一個探險家,唯有如此,我的人生才有可能像波曼爺爺的一半精采。他不斷鼓勵我,陪我共度無數個午後,在我身旁彎著腰,教我閱讀世界地圖。我們在地圖上釘了一連串紅色的大頭圖釘,用想像力策劃航線;他告訴我,有朝一日,我會發現許多令人驚奇的地方。回到家裡,我興高采烈地宣告志向,把厚紙板捲成筒狀貼在眼前,口中高喊「有陸地」或是「準備上岸慶功囉」,卻被我爸媽轟到外頭。我猜他們擔心爺爺給我灌輸太多不切實際的夢想,蒙蔽了更實際的企圖心,導致我無法自拔,無法朝向社會普遍認同的目標前進。大概是因為如此,所以某天媽媽把我拉到一邊促膝長談,告訴我,我不能當探險家,因為這個世界已經被探索完了。我生錯了時代,而且我心裡覺得被欺騙了。
我慢慢了解波曼爺爺大多數的故事根本不切實際,更覺得自己被背叛。他的童年故事尤其扯,他說他出生在波蘭,十二歲時被送到英國威爾斯的孤兒院。當我問他為什麼要離開父母時,他的回答永遠千篇一律:因為怪物要抓他。他說,波蘭的怪物多到讓他無法喘息。
「怎樣的怪物?」我睜大眼睛問道,這問題已經變成了一種例行公事了。「可怕極了,彎腰拱背,皮膚潰爛,眼珠烏漆嘛黑。」他說:「而且他們這樣走路!」然後他左搖右晃地追著我,宛如老電影裡的怪物,我則邊跑邊哈哈大笑。
他每次描述怪物,都會增添一些恐怖的小細節:他們散發惡臭,像腐敗的垃圾堆;他們身體透明,只看得見影子;他們的嘴巴裡藏著好幾條觸鬚,觸鬚會瞬間張牙舞爪地竄出來,把人捲進他們有力的口中吞食。不久之後,我就患上失眠的問題;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作祟下,我常常誤以為窗外輪胎和溼馬路的磨擦聲是怪物沉重的呼吸,也常把門縫的陰影幻想成扭動的黑灰色觸角。我害怕怪物,但是想到爺爺隻身和他們搏鬥、並得以存活下來訴說他的冒險故事,就覺得心情一振。
他在威爾斯孤兒院的故事也總是令我聽得出神。他說,那是個奇幻之地,專門保護被怪物迫害的孩子,島上每天豔陽高照,從沒有人生病或死亡。所有的孩子都住在一棟大房子裡,受一隻睿智的大鳥保護──至少他的故事是這麼說的。然而,隨著年紀增長,我心中也開始冒出問號。
「怎樣的大鳥?」那是七歲的一個午後,我懷疑地盯著爺爺問道。他坐在茶几的另一頭,故意讓我贏一局大富翁。
「一隻叼著菸斗的大老鷹。」他說。
「你一定以為我很蠢吧,爺爺。」
他手上那一疊橘橘藍藍的玩具鈔越來越薄。「我當然不會這樣想,雅哥(Yakob)。」我知道我一定刺激到他了,因為他始終無法完全擺脫的波蘭腔又跑出來了;他的「會」說得像「灰」。「想」說得像「賞」。一陣罪惡感襲來,我決定姑且順著他的話。
「但是為什麼怪物要傷害你?」我問道。
「因為我們和一般人不一樣,我們很特別。」
「怎麼個特別?」
「喔,各有各的特別之處。」他說:「有一個女孩子會飛,有一個男生肚子裡住著蜜蜂,還有一對兄妹可以把巨石舉過頭。」
我看不出他是否是認真的,但是我爺爺並非愛說笑話的人。他看穿我臉上的懷疑,失望地皺起眉頭。
「沒關係,你不一定要相信我的話。」他說:「我有照片為證!」他從折椅上站起身走進屋子,留下我一個人在戶外陽臺上。一分鐘後,他捧著一個老舊的雪茄盒回來,從裡頭抽出四張布滿折痕的泛黃照片,我不由自主地把身體湊向前。
第一張照片暗淡模糊,看似一套沒有人穿的衣服,否則就是穿衣服的人沒有頭。
「他當然有頭啊!」爺爺笑盈盈地說:「只不過你看不見。」
「為什麼?他會隱形嗎?」
「嘿,你真是小天才!」他挑了挑眉,似乎對我的推理能力大為驚嘆。「他的名字叫做米勒(Millard),很會搞笑的孩子。他有時候會跟我說:『嘿,亞伯,我知道你今天做了什麼好事。』接著他會告訴我我當天去了哪裡、吃了什麼、有沒有趁著四下無人偷偷挖鼻孔。他有時候像小老鼠一樣跟蹤人,因為他沒穿衣服,所以你看不到他,他很愛觀察!」他搖搖頭說:「我正想給你看這張,你看看。」
他遞了另一張照片給我。我看了一會兒,只聽他繼續說:「所以呢?有看出什麼嗎?」
「一個小女孩?」
「還有呢?」
「她戴著后冠。」
他用手指彈了彈照片的底部。「她的腳呢?」
我把照片拿到眼前細看,小女孩的腳並沒有踩在地上,但是她也沒有跳躍,──她似乎浮在半空中。我的下巴掉了下來。
「她會飛!」
「很接近了。」爺爺說:「她會飄浮,只不過她的自我控制力不好,我們有時候必須在她身上綁一條繩子,以免她飄走!」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她洋娃娃般的臉龐,壓抑心中的震撼。「這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他理所當然地回答,一邊拿走我手中的照片,並遞上另一張。這次是一個纖瘦的小男孩,他徒手舉起大岩塊。「維多(Victor)和他妹妹不太聰明。」他說:「但是,老天啊,他們真強壯。」
「他看起來並不強壯。」我看著男孩瘦弱的手臂說道。
「相信我,他很強壯。我有一次和他比腕力,他差點把我的手扭斷!」
不過最詭異的就是最後一張照片,那是一個人的後腦杓,上面卻畫著一張臉。
我一邊盯著最後一張照片,一邊聽波曼爺爺解釋。「他有兩張嘴,看到了沒?一張在臉上,一張在後腦杓,所以他才長這麼大塊頭、這麼胖!」
「但是這是假的。」我說:「這張臉是畫上去的。」
「當然啦,油彩畫的臉是假的,這是為了馬戲團表演。但是我告訴你,他真的有兩張嘴,你不相信嗎?」
我思考了片刻,看看照片,又看看我爺爺。他的表情真誠而開朗,他何必說謊?
「我相信。」我說道。
§怪物§
我忽然看到後院隱約有一絲微光。
我跑到紗門外,看到草坪上有一把被丟棄的手電筒,光束正好指向院子旁邊的樹林。人稱這片低矮的林地為「世紀林」(Century Woods),茂密的鋸櫚樹和敗壞的老棕櫚綿延一英里,正好隔開了迷陣村和隔壁社區。根據當地的傳說,樹林裡有許多毒蛇、浣熊和野豬。我想像爺爺獨自穿著浴袍失魂落魄地在其間游盪,滿口胡言亂語,心中不禁湧現一陣陰鬱悲涼的情緒。每隔一兩個星期,我就會在電視上看到某個老年人掉進蓄水塘裡、被鱷魚吞噬的新聞。最糟糕的狀況莫過如此。
我呼喊瑞奇的名字,沒多久他就沿著房子外圍飛奔而來,並且馬上發現我沒注意到的疑點:紗門上有一道長條割痕。他低聲吹了一聲口哨說:「割得真可怕,可能是野豬幹的,山貓也有嫌疑。你看看這些動物的爪子有多利。」
不遠處傳來一陣淒厲的狗吠,我們同時打了一個寒顫,互相使了一個不安的眼神。「或者是狗。」我說。原本孤獨的狗叫聲掀起連鎖效應,附近的好幾隻狗隨之哀嚎,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
「也有可能。」瑞奇點頭說:「我車箱裡有一把點二二手槍,你等我。」他說完就快步回車上取槍。
狗吠聲漸漸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嗡嗡不絕的蟲鳴,模糊而疏離。汗珠從我臉上一顆顆滴落。天色已暗,不過晚風忽然停了下來,靜止的空氣比這一整天下來還要悶熱。
我撿起手電筒,謹慎地往樹林方向邁進。我很肯定爺爺就在那裡面,不過到底在哪裡?我不會追蹤足跡,瑞奇也不會,但是冥冥中似乎有一股力量引領我;我的胸口感到陣陣悸動,溼黏的空氣彷彿在我耳邊細語,令我不敢停駐片刻。我像是一隻獵犬嗅到獵物的氣息,大步往灌木林前進。
在佛羅里達州的樹林裡奔跑舉步維艱,因為沒有樹木的地方都長滿高度及膝、葉片鋒利的鋸櫚,以及糾結、茂密的雞屎藤。我只能一邊盡力往前跑,一邊呼喊爺爺的名字,漫無目的地揮舞手電筒。我從眼角餘光瞥見一道白影,立刻朝它直奔而去,走近一看才發現那是我好幾年前遺失的足球,脫了色,也洩了氣。
就在我打算放棄、回頭找瑞奇的時候,忽然看見不遠處有一排看似剛剛被踐踏過的小棕櫚。我握緊手電筒走向前,發現附近的葉片上沾黏了深色的液體。我感到喉嚨一陣乾渴,努力站穩腳步,繼續順著足跡前進;越往前走,我的胃就感到越緊縮,彷彿身體對我發出警告。最後,壓扁的樹叢往外擴散,他就倒在上面。
爺爺仆倒在一片蔓生植物上,彷彿從高空上摔下來。他的雙腿往外張開,一隻手臂扭曲地壓在身體下面。直覺告訴我他已經死了。他的內衣被鮮血浸透,褲子破裂,一隻鞋子也不見了。手電筒抖動的光束在他身上游移,而我全身動彈不得,只能呆呆地望著他。重新調整好呼吸之後,我輕輕喊他的名字,他沒有反應。
我膝蓋無力地跪在地上,手貼著他的背部;浸溼衣服的血液依舊溫熱,我可以感覺到他短淺的呼吸。
我一隻手塞進他身體下方,慢慢把他翻過身。他還活著,不過生命跡象越來越微弱。他的眼神渙散模糊,臉頰凹陷、蒼白。這時候,我才看到他的身軀上有好幾道深刻的傷口,我頓時感到天旋地轉。這些傷口又寬又深,表面沾滿泥土;他剛才躺過的土地被鮮血浸成溼溼黏黏的泥濘。我不忍直視,一邊盡量撇過頭,一邊用他撕裂的衣服蓋住傷口。
我聽見後院傳來瑞奇的聲音。「我在這裡!」我放聲嘶吼,或許我應該多說些什麼,像是小心危險或是有血跡,但是我失去了語言能力。我心中想的只有爺爺應該在病床上壽終正寢,那裡應該寂靜莊嚴,頂多只有醫療器材的聲音,而不是死在這陰溼、發臭的荒郊野外,還有螞蟻在四周橫行,我這時才發現他顫抖的手上握著一把銅製的拆信刀。
一把拆信刀,這是他僅有的防身武器。我才把刀從他指間抽走,他的手就無助地抖動,似乎想抓住什麼,我只好握住他的手。我們十指緊緊相扣,他的手蒼白薄弱,上面布滿紫色的血管。
「我必須抱你離開這裡。」我一邊告訴他,一邊把一隻手塞進他背後,一隻手抱住他的大腿;正當我準備抬他起來時,他發出微弱的呻吟,身體頓時變得僵硬沉重,所以我只好把他放回地上。我不忍心再傷害他了,但是我也不忍心把他一個人留在這裡。我無能為力,只能等待,於是我輕輕拍去他手臂上、臉上,和稀疏白髮上的泥土。忽然間,我注意到他的嘴脣隱約在顫動。
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比悄悄話還要小聲。我彎著腰,把耳朵貼近他嘴邊;他神智不清地喃喃細語,混雜了英語和波蘭話。
「我聽不懂。」我輕聲說。我反覆呼喊他的名字好久,直到他的目光聚焦在我臉上,接著他忽然重重倒抽一口氣說:「快去島上,雅哥,這裡不安全。」
被害妄想症是他的老毛病。我握緊他的手,告訴他我們很安全,他不會有事。這是我今天第二次對他說謊。
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到底是什麼動物攻擊他,但是他完全聽而不聞。「快去島上。」他反覆地說:「你在那裡很安全,答應我。」
「好的,我答應你。」我還能說什麼?
「我以為我能保護你。」他說:「我應該早點告訴你的……」我可以看出生命正從他身上流逝。
「告訴我什麼?」我忍住眼淚問道。
「沒時間了。」他的聲音細微,接著他用力從地上抬起頭,一邊虛弱地顫抖,一邊在我耳邊用氣音說:「去找大鳥,去圈套裡,去老人葬身處的另一頭,一九四○年,九月三號。」我點點頭,但是他一定看得出來我聽不懂。他用最後的一絲力氣繼續說:「愛默生,那封信。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雅哥。」
他說完就倒回地上,全身虛脫,力量耗盡。我告訴他我愛他,而他似乎慢慢墜入自己的世界裡,他的目光從我臉上慢慢飄向後方星光點點的天際。
過了一會兒,瑞奇才從灌木叢中衝出來,看見倒在我臂中的老人,嚇得倒退一步。「天啊,老天爺,老天爺啊。」他邊說邊用手搓揉自己的臉,口中含糊地問著還有沒有脈搏、有沒有報警、有沒有在樹林裡看到什麼。這時,我的體內忽然湧現一股異常詭異的悸動,於是我放下爺爺的遺體,慢慢站起身,全身上下的每一個末梢神經似乎瞬間啟動,這是我從未有過的直覺反應。樹林裡有東西。沒錯,我可以感覺到。
樹林裡只有我們,没有月光,沒有動靜,但是我就是知道何時該舉起手電筒照向哪裡。那一瞬間,我在細微的光束裡看見了一張臉,那張臉跟我童年時期噩夢中常常出現的那張臉孔如出一轍。他冷冷瞪著我,一對眼珠彷彿漂浮在漆黑的液體中,碳黑色的皮膚上烙印著一道道深刻的紋路,背部明顯隆起,嘴巴令人作嘔的半張半閉,好幾根像鰻魚般的舌頭從口中伸出來竄動。我放聲大叫,而他一轉身就消失了;樹叢間傳來一陣窸窸窣窣的騷動。瑞奇也發現不對勁,他舉起點二二手槍,扣下板機,砰、砰、砰、砰。他說:「那是什麼?那到底是什麼?」但是他沒有看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他。我只能僵直地站在原地,任手中微弱的手電筒漫無目的地照著樹林。接著我大概失去了意識,只聽見他喊著,雅各、雅各!特教生!你還好吧?然後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隼夫人§
我聽見腳步聲,接著聽見有人交談。我全神貫注地想聽清楚他們在說什麼,但是聽不到。我不敢動,生怕輕輕一動就會牽動整個房子,造成土石崩落。我知道我無須恐懼,這應該只是那兩個喜歡饒舌歌的蠢孩子惡作劇,但是我的心臟砰、砰、砰疾速狂跳,內心深處原始的動物直覺告訴我:保持安靜。
我的腿漸漸麻痺,只好偷偷把重心轉移到另外一條腿上,好讓血液流通。腳下的土石堆鬆動,不知道什麼東西從木片瓦礫堆滾落,在一片死寂中顯得格外刺耳。交談聲忽然靜止下來,接著我頭上的木板吱吱作響,大片粉塵應聲撒落。我不知道誰在上面,但是他們一定知道我的位置。
我不敢呼吸。
然後,我聽見一個女孩子溫柔的說:「亞伯,是你嗎?」
我以為自己在做夢,安靜地等待女孩再次開口,不過等了許久,只聽見雨滴拍打屋頂的聲音,好似上千根手指輕輕在遠方輕彈。忽然間,上方亮起一盞小提燈;我抬起頭,好幾個孩子跪在洞口往下窺看。
我覺得他們似曾相識,卻想不起在哪裡見過他們,彷彿這些臉孔曾經出現在我若有似無的夢境中。我在哪裡見過他們?他們又怎麼會知道我爺爺的名字?
忽然間,一切都揭曉了。他們的服裝奇特,並非威爾斯人的一般衣著;他們肌膚蒼白,臉上沒有笑容;他們從上方俯視我,就好像我眼前散落一地的照片。我想通了。
我在照片裡見過他們。
說話的女孩站起身,仔細盯著我瞧。她手中捧著閃爍的光芒,那並非提燈或蠟燭,反倒像一團火球,而她正用赤裸裸的手捧著它。不到五分鐘前,我才看過這女孩子的照片;照片中的她和現在一模一樣,手中也捧著相同、詭異的火光。
我是雅各,我想這樣告訴她,我一直在找你。但是我的下巴不聽使喚,只能一動也不動地盯著她看。
我們經過一片樹林,山路寬闊明亮得像國家公園的步道一樣,接著來到一片花朵繁茂、造景精細的廣大草皮上,大房子就在眼前。
我訝異地觀察它,並非因為它陰森可怕,而是因為它美輪美奐。屋瓦沒有一片剝落,窗戶也明亮完好,記憶中陷落的塔樓和煙囪此刻氣宇非凡地指向天空,先前吞噬外牆的樹叢則與房子保持著一段安全距離。
他們領我走向石板鋪成的小路,爬上剛剛塗漆的臺階,來到門廊上。艾瑪雖然不再像起初一樣把我視為威脅,不過進屋前,她再度把我的手捆起來──我猜她只是想做樣子給別人看,好證明自己戰功彪炳,而我則是她的戰利品。她正要帶我進屋時,卻被米勒攔了下來。
「他的鞋上沾滿了爛泥。」他說:「不能讓他弄髒屋子,大鳥會大發雷霆。」他們默默地看著我把沾滿泥巴的鞋子、襪子一一脫下來;米勒又建議我把牛仔褲的褲管捲起,以免在地毯上拖行,我乖乖照辦。最後,艾瑪不耐煩得抓住我,把我大力拉進門。
記憶中的大廳難以通行,地上散布殘破的家具,但在此刻卻整齊寬敞。我們穿過大廳,前方的樓梯剛剛打過蠟,一張張好奇的臉孔在欄杆後、餐廳裡朝我們張望。餐廳大片的落石、粉塵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張長桌,桌邊圍滿椅子。這確實是我先前探索過的房子,但是一切都像被整修過一樣。先前的綠色霉斑不見蹤影,牆上是壁紙、護牆板和色調明亮歡樂的油漆。花瓶裡插著精緻的花束。地上腐朽的木材和纖維彷彿自行重組成舒適的沙發和扶手椅。陽光穿過高處的窗戶灑落一室,和先前蒙著一層灰、不見天日的景象截然不同。
我們最後來到面對後院的小房間。「我去通知院長,你看好他。」艾瑪對米勒說。我感到他的手抓著我的手肘,不過艾瑪一離開,那隻手就鬆開了。
「你不怕我把你的腦袋吃掉嗎?」我問他。
「不怎麼怕。」
我轉向窗戶,驚奇地看著外頭。庭院裡都是嬉戲的孩子,我曾經在泛黃的相片中看過中其中不少臉孔。有人在樹蔭下乘涼,有人玩著球,有人在色彩繽紛的花圃上互相追逐;這景象和爺爺所描述的樂園如出一轍。這裡就是那個奇幻島,他們就是那群可愛的孩子。如果這是夢,我希望我一覺不醒――至少別醒得太快。
遠方的草皮上,有人一腳踢得太大力,把球踢到修剪成動物形狀的樹叢上。放眼望去,外圍成排的樹叢都被修剪成奇幻故事裡才有的動物,高度與房子相當,彷彿捍衛著孤兒院,以免受到樹林的侵襲;這些動物包括長著翅膀的獅鷲獸、翹著臀部的人馬,還有人魚。兩個撿球的少年跑到人馬的旁邊,背後跟著一個小女孩,我立刻就認出她是爺爺照片中的「飄浮女」,只不過她並沒有飄浮,卻走得很慢,看起來舉步維艱,彷彿每一步都受到好幾倍的地心引力重重拉扯。
她走到男孩的身邊舉起雙臂,男孩拿著一條繩子繫在她的腰間。她小心地脫下鞋,身體像個氣球一樣緩緩升空,我看得瞠目結舌。她不停地往上飄,腰間的繩子越拉越緊,最後她飄浮在距離地面十英尺高的空中,只有兩個男孩在下面拉著她。
女孩不知對男孩說了什麼,男孩點點頭,然後把繩子越放越長。她沿著人馬的側身緩緩升空,飄到人馬的胸口處時,她伸手去樹枝間撿球。不過球卡得太深了,她看看下方,無奈地搖搖頭,男孩才捲著繩子把她拉回地面。她穿回加重的鞋子,最後才解開繩子。
「看戲看得很過癮吧?」米勒問道,我安靜地點點頭。「要撿球,有很多更簡單的方法。」他說:「不過他們知道有觀眾在看。」
外面另一個女孩往人馬方向走去,她看起來十七、八歲,外型狂野,雜亂的頭髮像鳥巢般糾結成一團。她彎腰拉住人馬的長尾巴,把枝葉纏繞在自己的手臂上,接著專注地閉上雙眼。不一會兒工夫,我看見人馬的手動了。我凝視著窗外,全神貫注地盯著那片綠葉,心想一定是風吹的,但是此時就連它的手指也一一動了起來,彷彿逐漸從沉睡中甦醒。我驚愕地看著人馬彎曲巨大的手臂,一手探進自己的胸口掏出球,並把球投擲給歡呼的孩子們。球賽繼續進行,髮型狂亂的女孩放下人馬的尾巴,人馬才再次陷入靜止中。
米勒的呼吸在玻璃上形成一片霧氣,我一臉不可思議地轉向他。「我無意失禮。」我說:「但是你們到底是什麼?」
「我們很獨特。」他回答,聽起來有些疑惑。「你不是嗎?」
「我不知道。我想我沒什麼獨特的。」
「真可惜。」
「你為什麼放開他?」背後傳來吆喝的聲音,我回頭看見艾瑪站在門口。「喔,算了。」她一邊說著,一邊走到我身邊抓住繩子。「走吧,院長要見你。」
我們來到房子的另一頭,一雙雙好奇的眼睛透過門縫、躲在沙發後頭偷窺我們。我們走進一間光線明亮的大廳,大廳中間擺著花樣精緻繁雜的波斯地毯,地毯上的高背椅上坐著一位正在打毛線的婦女。她外型出眾,從頭到腳一身素黑,長髮在頭頂上盤成完美的圓形髮髻,手戴蕾絲手套,高領襯衫的領口完全包覆著喉嚨──她的打扮就像這房子一樣一絲不苟。雖然那只砸爛的大木箱裡並沒有這個女人的照片,但是我不難猜到她是誰。這就是裴利隼女士。
25 開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作者印簽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