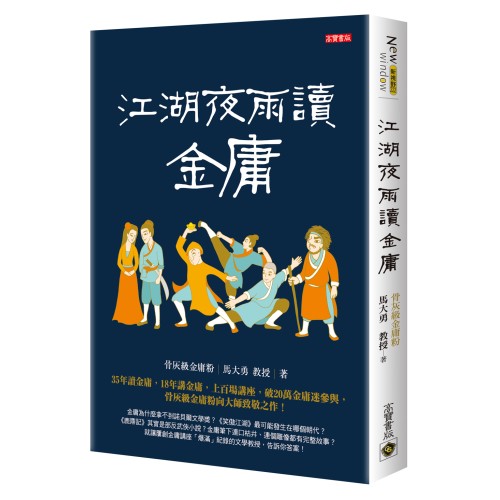-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 妳是無邊月色,亦是我的煙火人間── ❞
★ 實力派古言掌門人 尤四姐 宮廷權謀代表作,《浮圖緣》前傳!
★ 多智近妖初代督主×大智若愚江湖女兒。
★ 晉江積分19億,影視版權已售出,火熱籌備中。
世人皆言司禮監督主梁遇,
執掌皇權,殺伐倥傯,把持朝堂。
卻無人知曉,在琉璃瓦重簷殿之下,
是愈發空蕩硬冷的心,與漫長孤寂。
直到找著月徊,道破身世之後,
梁遇再也無法抑制對煙火人間的無盡渴求。
親眼見皇帝大婚、立后,
月徊終於看明白帝王之愛,是雨露均霑、薄情寡義。
藉著梁遇南下剿滅亂黨之機,一同離開皇宮,
卻在搖曳的船板上,陡然直面梁遇對自己的感情。
他們是兄妹,怎可生出這樣的歧念?
但如果,他們並非親人呢?
新皇初立,朝堂、境內、邊關,各方勢力湧動,
離了梁遇的皇帝如失了左膀右臂,處處掣肘,寸步難行。
為了維繫皇權,他必須擁有將梁遇綑綁在身旁的籌碼──月徊。
第二十章 世事倫常
掌印督主,向來是司禮監和廠衛眼裡高高在上的存在,很多時候對於那些沒有機會面聖的人來說,他就是皇權。可如今受了傷,臥在床褥間,雖然痊癒後依然會是那個城府似海,手握酷刑的老祖宗,可以目下情勢來看,竟是從神變成了人。
鄭太醫把了脈,又開藥箱取銀針,在先前強行閉闔的傷口上施針,把裡頭瘀積的污血排出來。
又是一輪傷筋動骨,昏厥的梁遇輕輕呻吟起來,月徊的心一下子就碎了,蹲在床前握住他的手說:「哥哥……哥哥您忍一忍,把毒血放出來就好了。」
雪白的巾帕蘸了血,一重又一重扔進銅盆裡,直到把污血都吸完,才重新灑上藥粉包紮起來。月徊惶然追問:「太醫,我哥哥他怎麼樣了?」
鄭太醫鬢角都濕了,顧不上擦汗便回身開藥,一面道:「姑娘別急,先前是出血不止,才暫且縫合了傷口。傷口閉闔,皮下來不及排出的血就攢成了瘀血,只要把這血清除,等熱一退,好起來比慢慢溫養還快呢。」
月徊聽了心下一鬆,回頭再看床上氣息奄奄的人,暫且看不出好轉的跡象,又不能再說什麼,只好等著小太監煎藥回來。
那廂楊愚魯和秦九安合力將人翻起,讓梁遇側臥著,他的氣息相較之前略微平穩了些,月徊忙又輕聲喚:「哥哥,您好點兒了嗎?」
他分明是聽見的,卻不願意睜眼,蹙著眉微微別開了臉。月徊頓時有些訕訕的,心道自己受了委屈,他倒來脾氣了呢,要不是看他有傷在身,她早就不理他了!
楊愚魯忙打圓場,「老祖宗尚且沒氣力,不過依我看,像是比先前安穩了些。」
高漸聲道:「要是能睡會兒倒是好事,興許一覺醒來燒就退了。」
可照眼下局勢來看,要睡著只怕很難。
外頭狂風過境後,那些廠衛正掌著燈尋找遇難的人,隱約聽見嘈雜的喊聲,不一會兒就有人在門前叫少監,說十二團營的張千戶找著了。
死了一個千戶,實在是件大事,秦九安忙追了出去。
月徊見楊愚魯臉上焦急,便道:「楊少監您也去吧,這兒有我呢,我能照顧好哥哥。」
楊愚魯有些遲疑,「老祖宗這樣,我實在不放心……」
梁遇終於開口了,輕喘口氣道:「你去吧。那些兄弟……想法子找全,不能讓他們……葬身在魚腹。」
楊愚魯道是,「那您……」
梁遇臉上的潮紅消退了些,只是唇色還發白,緩了緩道:「我不要緊,你去辦事吧。」
於是艙房裡人又褪盡了,只餘鄭太醫和兩個徒弟來回忙碌著。
月徊這時對哥哥有了新的認識,她一直以為他手握大權,不管別人死活,可如今看他對身邊的人,不可說不講江湖義氣。
那些辦差的兵勇,照說死了多少都不放在朝廷眼裡,況且是在海上,要是把屍首撈上來,就得另派幾個人護送他們回去,又是人力又是物力,對於只重結果的司禮監和廠衛來說,確實很不值當。但掌印發了話,底下的人就得照辦,很大程度上來說,那些枉死在海上的人能不能魂歸故里,都靠他一句話。
幸好他有人情味,幸好他不是那麼冷血。月徊長出一口氣,見門上小太監端藥進來,忙上前接了手。其實說到根兒上,就算不是親生的哥哥,他們也做了那麼多年的兄妹。爹娘如今是不在了,要是在,難道還不認這個兒子嗎!
只是心裡有些彆扭,倘或沒有風暴裡的那一齣,哪怕知道了兩個人不是嫡親的,至多有點遺憾,心境上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她可能會繼續尊敬他,繼續覬覦他,那種覬覦純粹是兄妹間的胡鬧,帶著點豔羨和驕傲,恨不得大聲告訴所有人,「這財大勢大的美人兒是我哥哥」。
結果一切急轉直下,到現在她都沒想明白那件事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好在她這人心大,想著他當時也許神志不清了,可以不去計較。等他身上的傷好了,腦子不糊塗了,要是不願意再提及,這事過去也就過去了。
她端著藥碗吹了又吹,送到他跟前說:「哥哥,喝藥吧……我來餵您。」
梁遇聽見她一口一個哥哥,試探過了,心裡的那團火冷卻成灰,再也沒有顏面面對她了。
「讓別人來伺候。」他垂著眼睫道:「妳去休息。」
月徊聽了微一怔忡,「這時候全在忙,沒人顧得上您,還是我來吧。」
她知道他尷尬,但這海滄船就這麼大,到廣州的路還有很長,就算迴避,能迴避到幾時?往後真如參商,再不相見嗎?
梁遇被她說得彷彿遭到遺棄,世上只有她還願意搭理他似的,一時窒了口。於是低垂的眼睫更低垂,不單低垂,還略微別開了臉。
月徊見他這樣,拿勺子小心翼翼舀了藥,也不多言,就貼在他唇上。他的嘴唇生得極好看,飽滿潤澤,要是抿上口脂,絕對是畫像上那種檀口。可這唇……現在也讓她心慌。她不敢直著眼瞧,跪坐在榻前的腳墊上,也有芒刺在背之感。
他彆扭再三,讓不開那湯匙,最後只好勾起脖子把藥喝了下去。她倒是餵得極耐心,就那麼一勺一勺,不知道這藥有多苦。慢喝等同細品,他沒辦法了,掙扎著撐起身,一口氣把藥全灌下去,然後調開視線,把空碗遞還了她。
兩下裡相處正尷尬,邊上鄭太醫趨身上前一步,呵著腰道:「廠公且好好休養,傷勢固然沉重,但不傷及臟器,應當沒有大礙的。這兩日卑職會替廠公調整方子,藥吃上個三五日,自然就痊癒了。」說罷又轉身,把一個精瓷的小瓶子交給月徊,「姑娘費點兒心,這藥每隔日半就要換新的,姑娘手上力道輕些,替廠公換藥正相宜。」
這是什麼話,為什麼都是她正相宜呢,伺候茶水就算了,連換藥怎麼都是她?
月徊正想表示異議,誰知鄭太醫連瞧都沒瞧她一眼,帶著徒弟轉身便往外去了。她拿著藥,腳下茫然追了兩步,再回頭時看見他的目光,泠泠的,說不盡裡頭摻雜了多少情感,只是見她望過來,又匆忙闔上了眼。
梁遇的心思百轉千迴,他桀驁且孤高,這事過後怕需要很長的時間調整,也或許從此斷了這份念想,就一心同她做兄妹了。當然有了這一回,兄妹之情再也純粹不起來了。
月徊魯莽直爽,也有她的好處,哪怕臉頰滾燙,她也壯起膽兒走到他的床榻前,撐著膝頭彎腰問:「您好點兒沒有?」
他「嗯」了聲,藉錦被,遮住了半張臉。
「這會兒還燒嗎?」她探手想去觸他額頭,他卻把整張臉都藏進被褥裡。
月徊看看自己伸到半途的手,無奈地收了回來,待平了平心緒方道:「您打算這輩子都不見我了麼?剛才的事,我能體諒您,您是受了重傷神思恍惚,又覺得自己會死在這場風暴裡,這才把我當成了別人。我不怪您,我這人生來大方,從不小家子氣,您是我哥哥,哥哥親一下怎麼了,又不是讓外人親了。您小時候不也親過我嗎,為什麼我四五歲的時候您能親,現在就不能了?就因為長大了嗎?我記得您說過的,我在您跟前永遠是孩子……還有一句俗話,那個……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她真是豁出去了,替他找了一堆生硬的理由,以此為他開脫。什麼小時候親過,四五歲時能和現在一樣麼?親一口臉頰,和吻上嘴唇一樣麼?
這件事不說破,永遠蒙著一層紗,她的腦瓜子長得怪,自己琢磨琢磨,能捏造出所謂的「別人」來,順便把自己變成替身,然後自怨自艾一通,覺得自己十分可憐。
他終於從被褥間抬起了頭,身上一層熱汗,不是因為傷勢的緣故,是因為心頭星火復燃。
中氣雖不足,但他仍舊一字一句反駁了她的話,「我清醒得很,由頭至尾都很清醒。沒有別人,也和小時候無關,我就是……就是喜歡妳。也許妳會拿我當怪物,我不在乎。」說著頓下,勻了口氣方又道:「從我知道自己……不是梁家人起,我就動了心思。妳罵我無恥也好,喪盡天良也好,我都認了……我就是喜歡妳,沒來由地喜歡妳,今日如此,他日亦如是。」
月徊腦袋裡嗡嗡作響,什麼無恥啊,什麼喪盡天良啊,這些都不是最要緊的,最要緊是他說喜歡。
喜歡什麼?喜歡她?天底下怎麼會有這麼可笑的事!她咧著嘴,表情裡帶著驚惶的味道:「您喜歡我什麼?我這麼個沒出息的丫頭,除了能吃什麼也不會,您喜歡我?再說您是我哥哥,您怎麼能喜歡我呐?」
就算回來只有半年,哥哥妹妹也很親厚,她垂涎三尺著,心裡卻越不過那段兄妹的關係。說實在話,她真如自己評價的那樣沒出息,明明之前還想入非非,還可惜生在一家子。現在有機會了,他也親口說喜歡她,為什麼她反倒退縮了?
打量他一眼,是他美貌不再,臉長歪了嗎?並不是。他的好看,是一時有一時的韻致。在錦衣華服統領廠衛時,他是燦若驕陽的掌印;燕居深宅寬袍緩袖時,他是一杯梨花白酒;眼下呢,受了傷,平時趾高氣昂的人一旦臥床,又會顯出另一種羸弱的美態來……這人是不能細看的,細看了會上頭,會招人夜裡做夢。
那是為什麼?還是因為自己的怯懦!她以前膽兒肥起來,想過看臉過一輩子,如今人家不要當她哥哥了,就想讓她看臉,結果她又嚇得肝兒顫了。
細細琢磨,還是敬畏成了習慣,她心裡尊敬他,哥哥該是高天小月,可望不可即。月亮高高掛著很美好,一旦落下來,那可是要砸死人的。
梁遇呢,比他自己想像的更勇敢。本來她裝糊塗推三阻四,他是打定了主意不再繼續下去的,但就此放棄,又覺得不甘心。月徊這樣的性子,你給她一包糖,哪怕是隔著河,她游都能游過來接著。可你要是隔著一扇窗和她不談親情談愛情,再開窗的時候,窗後怕早就沒人了。
南下是個好機會,既然心裡放不下,那就撞他個頭破血流吧。
「那麼多回,我要找女人,妳為什麼不答應?」他支著身子問她,「不是因為……因為妳心裡也有我,才多番阻撓的嗎?」
月徊有點傻眼,這個問題實在很難回答。她確實對他有獨占欲,覺得才認回的哥哥,憑什麼忽然跑來個女人,就分走哥哥一大半的關愛!她希望哥哥所有目光都在她身上,希望哥哥的所有溫情只對她一個人生效。她不喜歡哥哥和別人打情罵俏,因為哥哥捧著別人,就騰不出手來捧她了……這些私心她怎麼好意思說出口,所以在他看來,就是對親哥哥生出了不倫之情吧!
月徊有點沮喪,看來過去自己的舉動太倡狂,才一步一步把他引進陷阱裡,這麼說來他才是受害者。她難堪地搓了搓手,「我是怕您被人騙了,宮裡那些女人,都是看中了您的權勢。」
梁遇牽著唇角自嘲地笑起來,「我這種人,還盼著別人對我用真情?」一面長吁著,「不過是拿權,換別人的好臉子罷了。」
再強悍的人,骨子裡也有觸碰不得的弱點,月徊聽了他的話,又覺得他那麼可憐,「哥哥,您別這麼說,世上沒有人比您更好,真的。」
「我這麼好……」他調轉視線看向她,「妳為什麼不喜歡我?」
他步步緊逼,逼得月徊心在腔子裡亂竄,她支支吾吾說:「那……不是……因為您是梁日裴麼!日裴月徊,這是爹娘取的名字,他們盼著咱們將來互相扶持,沒想讓咱們……咱們……」
「做夫妻?」他把她的話補全,心裡只覺難過。到現在才真正明白盛時的話,為什麼那對做了夫妻的兄妹,會被人戳一輩子脊梁骨。爹娘沒有發話,私相授受即為偷,是不知羞恥,是逾越倫常,該遭天下人口誅筆伐。如果爹娘還活著那多好,他就算去跪,也要求娶月徊。然而他們不在了,那兩面牌位,能給他什麼回答?
他閉上眼睛,執拗地喃喃著:「不管妳答不答應,我就是喜歡妳。妳知道就成了,不必回應。」
這話說的……月徊眨著眼睛,摸了摸自己的後腦勺,「知道就成了……我知道後要炸廟,哪兒還成得了!」
覷覷他,那股子一言九鼎的勁兒在眉宇間,發號施令慣了,就是這麼霸道。
月徊退了一步,「這事先不談,您身上還沒好,不宜說話置氣,還是先養著,等痊癒了再商量,啊?」
她像敷衍孩子,可梁遇心裡卻憋著氣。她不是碼頭上的通達者,市井裡的開闊人兒嗎?到臨了拖泥帶水,沒有一句痛快話,讓他失望。
他嘆了口氣,「是我讓妳為難了。」
月徊不知該怎麼回答,為難確實是為難,從哥哥變成路人,又從路人萌生出另一種情愫,另一種關係,她的腦子不夠使,一時轉不過彎來。
梁遇說了那麼多話,已經把殘存的力氣用完了,後來便昏昏沉沉,身上熱度不得消減,折騰到天亮,才逐漸好轉。
清晨的時候月徊走出艙房,方看清鷹嘴灣附近海域的慘況。水面上到處散落著碎裂的船木,海水拍打著遠處的礁石,攪起一重又一重的浮沫。
那些廠衛一夜不得休息,仍舊撐著哨船四下尋覓。恰好馮坦經過,月徊叫了聲大檔頭,「那些落水的人,現在怎麼樣了?」
馮坦道:「救上來三個喘氣兒的,打撈了七具屍首,剩下五個怕是懸了,能不能找回來,得看老天爺開不開恩。」
話音才落,聽見下面吵嚷起來:「有了、有了……」
月徊忙趴在船舷上看,眾人合力又從水裡拖上來一個,濕漉漉的屍身,死沉死沉。原本活蹦亂跳的人,缺了一口氣就變成了物件,月徊看得心驚,忙縮回身子。
馮坦負著手嘆息,「要是刀劍上出了事,也算死得其所,落在水裡頭淹死,可不窩囊嘛!」說罷朝艙樓望了眼,「督主怎麼樣了?好些了麼?」
月徊道:「這會子燒退了,等睡醒再換一回藥,他身底兒好,恢復起來應當很快的。」
馮坦點了點頭,負著手說:「海上潮濕,傷口養起來怕沒那麼利索,姑娘還得多費心。」
月徊不大滿意他們老是有意無意的撮合,心裡頭又埋著事,便試探著問:「大檔頭,您幾位知道我和他是一家的吧?」
馮坦說知道啊,「又不是親的。」語氣十分篤定且不屑。
這就是說,他們眼裡頭只要不是至親,就沒有那麼多的阻礙。當初梁遇找回她時,對外宣稱是族親,後來長公主大鬧也沒能把這事捅破,到這會兒竟是歪打正著了。
是不是天意?外人看來真是一點毛病也沒有,弄得她現在想迴避,卻受不住旁觀者眾口鑠金。他們全是梁遇的手下,且個個對他俯首貼耳,在他們心裡太監找個對食不容易,橫豎人都不齊全了,喜歡誰要誰,全憑高興。
月徊嘆了口氣,在甲板上慢慢轉悠了兩圈。日出了,一輪太陽從水底下升起來,清早的太陽不刺眼,圓圓的大臉盤子,像一個扔到水裡頭的剔紅漆盤。
馮坦也閒得慌,在邊上看了她半天,「大姑娘,您這是有心事啊?」
月徊說沒有,「我窩了一整夜了,出來發散發散。」
馮坦道:「發散完了就回去吧,沒的督主醒了跟前沒人。」
月徊「嘖」了一聲,「我是丫頭嗎,一會兒也離不得!」說完了還氣惱,下勁兒給他上了一層眼藥,「大檔頭,大家全在忙乎呢,就您戳在這裡,是想偷懶嗎?」
馮坦被她擠兌得打噎,最後哼了一聲,拂袖往船尾去了。
唉,月徊有點傷感,難得出來,本以為去兩廣的路上全是高興事兒,可惜又遇風暴,又披露身世的,鬧了這麼一大套。本來她是個愛湊熱鬧的人,如今熱鬧到了自己頭上,便覺得百無聊賴,實在不該出來這一遭。
想想小皇帝,那是頭一個說喜歡她的人,要是還留在宮裡,不說當娘娘,至少錯開了這驚人真相,梁遇的祕密興許就一輩子埋在肚子裡,一輩子當她的好哥哥了。
她回身望了望艙房,裡頭的人不知醒了沒。換藥的時候到了,遲了怕耽誤傷口,這就回去,心裡又犯嘀咕。最後磨蹭了會兒,還是不情不願折返,進門的時候見梁遇正費勁地坐起身來,她嚇了一跳,忙上去攙扶:「您要什麼,吩咐一聲就成了,何苦自己起來。」
梁遇試圖抽回手,冷著臉道:「這裡不用人伺候,妳出去。」
傷成這樣還嘴硬,身上的傷口可不會因他位高權重就不為難他。
月徊知道他心裡彆扭,眼下不和他計較,他要掙脫,她反倒攙得愈發緊。等他站穩了,才又問他:「您究竟要什麼?要喝水麼?您站著,我去倒。」
梁遇眉眼間有焦躁之色,「我不要喝水,妳先出去。」
「我出去了您怎麼辦?萬一再碰著了摔著了,這麼多人等著聽您號令呢。」她大義凜然了一番,又暗暗嘀咕,「該使性子發脾氣的是我才對,我都大大方方的,您還鬧什麼……再胡攪蠻纏,把你從船上扔下去!」
梁遇終於沒轍了,用力閉了閉眼,然後精疲力盡道:「我要如廁,妳先出去,成不成?」
月徊「啊」了聲:「您要如廁?」
梁遇臉上不大自在,「喝了那麼多湯水,難道不用如廁麼?」
尺寸(公分)14.8*21*2.04
開本 25
頁數 320
第二十章 世事倫常
第二十一章 月影朦朧
第二十二章 天青如洗
第二十三章 運籌帷幄
第二十四章 慈悲為劍
第二十五章 日裴月徊
第二十六章 未及消寒
第二十七章 魂斷西州
第二十八章 玉宇風息
尾聲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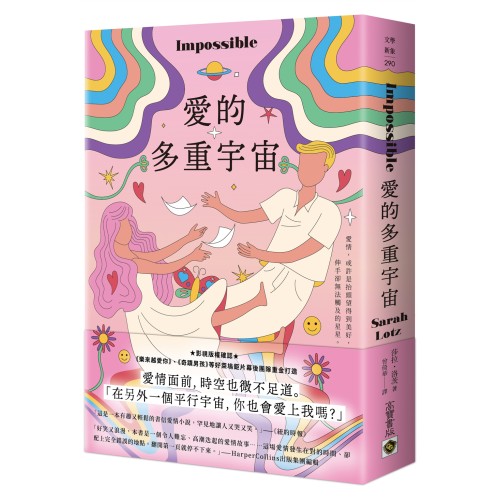
(六)套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