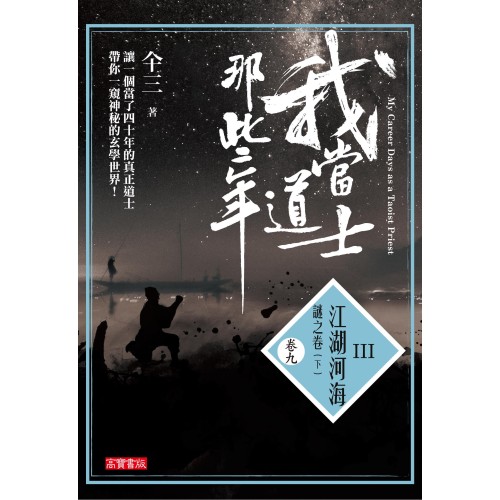-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三十週年‧全新中譯本★
★三十週年‧全新中譯本
★收錄三十週年新版序
★冠軍暢銷作家譚恩美成名作
★襲捲歐美文壇,華裔文學代表作
★《紐約時報》經典暢銷書
★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國家圖書評論家獎
★同名電影由柏林影展銀熊獎得主王穎執導、金獎大導奧立佛‧史東監製,
榮獲美國國家評論協會十佳電影獎
★全球超過二十種語言版本
「對我而言,《喜福會》是我珍惜一輩子、一生難得一次的閱讀體驗。」
──Kevin Kwan(關凱文),《瘋狂亞洲富豪》作者
「擁有神話般的魔力。」
--《華盛頓郵報》
「文字優美,出類拔萃。」
--《紐約時報書評》
這就是我愛母親的方式。
我在她身上看見真正的自己,就藏在這身皮囊下,深入我的骨子裡。
四位來自中國各地的女性,逃離封閉社會與專制父權,遠渡重洋移居美國舊金山,紮根生子。她們創辦一起聊天、打麻將的聚會──喜福會,分享彼此對故鄉的回憶、對故人的失落、對未來的希望。
四個在美國出生的華人女兒,在美式文化與中式教育的衝突中成長,承受母親的期望與壓力。長大成人後,她們與母親重新展開對話,探尋母親背負一生、神祕多舛的過去。
四對母女傾訴各自的回憶與心聲,兩代的隔閡與矛盾無法用三言兩語理清,但她們漸漸看見了真正的彼此。無論心中有多少糾結,母女之間的愛依然跨越一切,深刻入骨。
【全球盛讚】
「令人驚豔……《喜福會》帶給我們的世界令人目眩神迷。」
──《洛杉磯時報》
「令人印象深刻……描寫了兩個世代間強烈的愛與誤解。」
──《紐約客》
「強而有力的成就……豐富描寫現實生活中苦甜交織的矛盾。」
──《紐約日報》
「非凡的處女作。每位女性倒敘講述著自己的故事,她們的女兒回憶在兩種文化中成長所遇到的問題,充滿了智慧、幽默、愛以及悲傷。」
──《奧蘭多前哨報》
「身為美國人、女人、母親、女兒、妻子、姊妹與朋友是什麼樣子?在這本非凡處女作的十六個錯綜複雜、環環相扣的故事中,譚艾美描繪了這些令人煩惱,同時又充滿愛意的關係與羈絆。」
──《舊金山紀事報》
「誠實、感人、充滿勇氣。譚恩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中國、華裔女性與她們的家庭,以及母女之間謎一般的牽絆。」
--艾麗絲˙華克,普立茲小說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
千里鵝毛
這位老太太記得好幾年前在上海,傻乎乎地花大把鈔票買了一隻天鵝。市場小販吹噓這隻鳥曾經是隻鴨子,終日引頸期盼,渴望變成一隻鵝,現在看哪!——牠美得讓人不忍殺來吃。
後來,她帶著那隻天鵝千里遠渡重洋,翹首引領著美國。旅行途中,她輕聲細語地對天鵝說:「在美國,我會生一個像我的女兒。但在那裡,沒人會說她的價值是以丈夫打嗝聲是否響亮來衡量;在那裡,沒人會看不起她,因為我只會讓她說道地的美式英語。我會讓她衣食無憂,不再滿腹苦水!她會體會我的用心良苦,因為我會送她這隻天鵝——一隻成長得超乎期望的鳥。」
但當她抵達國外時,移民官將天鵝從她懷裡抱走,徒留女人揮舞著雙臂,只剩一根鵝毛作紀念。然後她不得不填寫一大堆表格,以至於忘了她為何而來,又留下什麼。
現在她老了,生了個女兒只會說英語,沒吃過什麼苦,滿肚子都是可口可樂。長久以來,這位老太太一直想把鵝毛給自己的女兒,告訴她:「這根羽毛雖然看起來不值錢,卻是來自遠方的禮物,帶著我的全部心意。」而她苦苦等待,年復一年,直到能以流利的美式英語告訴她的那一天。
喜福會
胡菁妹
父親要我加入喜福會成為牌腳之一。我是為了代替母親,自從她兩個月前過世後,她麻將桌的座位就一直空著。我父親認為她是被自己的思緒扼殺了健康。
「她腦海有一個新念頭。」父親說:「還來不及說出口,這個念頭就膨脹到極致,最後爆炸開來。那一定不是件好事。」
醫生說她死於顱內動脈瘤破裂,她喜福會的朋友說她就像兔子一樣,事情尚未完成就走了。我母親本該主辦下次喜福會的聚會。
她過世前一週,曾打電話給我,聲音充滿活力,自豪地跟我說:「妳琳姨在喜福會煮了紅豆湯,下次我要煮芝麻糊。」
「別這麼愛現。」我說。
「我不是愛現。」她說兩種甜湯幾乎一樣——差不多(chabudwo),又或許她說的是不同(butong),完全不一樣。這是中文的一種表達方式,表示雙面含意中較好的那個意思。我永遠記不住從開始就無法理解的事情。
母親於一九四九年開始在舊金山辦起了喜福會,就在我出生前兩年。我爸媽正是在這一年離開中國,帶著一個硬皮箱,裡面只裝了時髦的絲綢洋裝。母親上船後向父親解釋,她沒時間收拾其他衣物,但他仍拼命地翻開滑順的絲綢,找他的棉衫和毛呢長褲。
抵達舊金山後,父親要母親把那些閃亮的衣服藏起來。她身上穿著同一件棕色格紋旗袍,直到歡迎難民協會(Refugee Welcome Society)遞給她兩件二手衣,給美國女性穿都嫌過大。此協會是由一群頭髮花白的美國修女組成,他們全是第一華人浸信會(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的成員。由於收了禮物,爸媽拒絕不了他們的邀請去了教會,也不好無視這些老太太提出實際可行的建議:參加每週三晚間的福音課,與之後週六早晨的詩班練習,以改善英語能力。我爸媽就是這樣認識了徐家、鍾家和聖.克萊兒家。我母親感覺這些家庭的女人在中國也有難以啟齒的悲慘過去,並希望他們不要用自己的破英語陳述那些往事,或至少她認得出來這些女人臉上麻木的神情。而當她告訴他們喜福會的想法時,她注意到他們快速遊移的眼神。
喜福會這個想法來自我母親的回憶,發生在她第一段婚姻嫁到桂林(Kweilin)的時候,當時日本人還沒入侵中國。所以我認為喜福會是她在桂林的故事。每當她覺得無所事事,碗盤洗了,那張富美家(Formica)的桌子擦了兩遍,而父親坐著攤開報紙,抽著寶馬(Pall Mall)菸,警告不要打擾他時,她就會跟我說這個故事。母親會從盒裡拿出素不相識的親戚從溫哥華寄來的運動毛衣,剪開毛衣底部,拉出一根彎曲的紗線固定在一塊厚紙版上。當她以一種搖擺的節奏捲線時,便開始說出她的故事。這些年來,她一直告訴我同一個故事,唯獨結局變得更加黑暗,讓她的生活蒙上一層綿延不絕的陰影,最終也落在了我的身上。
「在親眼見識桂林的風光以前,我曾夢見那裡。」母親用中文開口說:「我夢到蜿蜒曲折的河流兩岸山石嶙峋,河岸長滿了青苔。山頂上覆蓋著白霧。若能順流而下,吃那些青苔果腹,就有足夠體力爬上山峰。即使失足滑落,也只會掉到一片柔軟的青苔上,開懷大笑。一旦登上山頂,就能將所有景色盡收眼底,所感受到的幸福,足以讓生活無後顧之憂。
「在中國,桂林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地方。直到我去了那裡,才意識到我的夢想是多麼破舊,想法多麼貧瘠。當我看到群山時,我笑得顫抖不已。山頂看起來就像一顆巨大炸魚頭,試圖從一大桶油中跳出來。視線每越過一座山,我都能看到另一條魚的影子,一條接著一條。然後雲層稍微飄移後,群山突然間成了巨型象群緩慢朝我走來!妳明白嗎?山腳下有秘密洞穴,裡面是一整片的懸岩,長成高麗菜、冬瓜、蕪菁和洋蔥的顏色及形狀。這些景色的古怪和絢麗是妳意想不到的。
「但我去桂林的目的不是為了欣賞美景,我前夫帶著我和兩名尚在繈褓的嬰兒到桂林,因為他認為那邊很安全。當時他是國民黨的軍官,他把我們安置在一個二層樓的小房間後,便前往北方,去了重慶(Chungking)。
「我們知道日本人打贏了,即使報紙否認這件事。每天無時無刻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湧進這座城市,擠在人行道上,尋找落腳的地方。這些人來自四面八方,不論貧富貴賤,上海人、廣東人、北方人,不只中國人,外國人及各宗教的傳教士也來了;當然還有自視甚高的國民黨軍官。
「整座城市變得魚龍混雜。要不是日本人,這群形形色色的人絕對會找到理由吵起來。妳明白嗎?上海人和北水農民、銀行家和理髮師、黃包車夫和緬甸難民,誰也看不起誰,即使大家共用一條人行道,一起上吐下瀉。我們都一樣髒臭,但每個人都在抱怨別人的味道難聞。妳說我?噢,我討厭美國的空軍,他們一直盯著我的臉發出調笑的聲音,使我羞得滿臉通紅。但最可怕的是那些北方農民,他們會用手擤鼻涕,四處推擠,身上還帶有骯髒的病菌
「所以妳可以知道,桂林對我來說已失去吸引力。我不再去爬山,然後說這山有多麼漂亮!我只會想日本人到了哪座山丘。我一手托著一個寶寶,待在屋裡陰暗的角落,坐立難安。當空襲警報響起,我和鄰居一躍而起,彷彿野生動物般的躲進深穴中。但人不能在黑暗中待太長時間,妳內心某些東西會開始消退,會像餓壞了一樣,瘋狂渴望光亮。我可以聽見外頭傳來的爆炸聲。碰!碰!還有落石的聲音。我的內心不再渴求高麗菜或蕪菁形狀的懸岩,我只看見垂著腸子的古老山丘,可能崩塌壓到我身上。妳能想像這種情況嗎?既不想待在裡面,也不願出去,什麼地方都不想去,只想消失?
「隨著轟炸聲越來越遠,我們會回到外面,像是新生小貓重新回到那座城市。而每次看見群山映襯著如火燒一般的天空,沒有被炸開來,都讓我覺得很驚訝。
「我在某個夏夜有了舉辦喜福會的念頭,那天非常熱,連蚊子都會被熱暈,濕熱的天氣會讓蚊子翅膀變重。到處都很擁擠,沒有新鮮空氣。下水道傳出難以忍受的氣味,一直飄到我二樓房間的視窗,臭味無處可去,只能進到我的鼻子裡。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我無時無刻不聽到尖叫的聲音,不知道是農民切開逃跑豬隻的喉嚨,還是軍官把擋路的農民打個半死。我沒有走到窗邊查看,那有什麼用?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我需要找事情做,幫我前進。
「我的想法是找齊四個女人,各坐在麻將桌一側。我知道要找誰來,他們都跟我一樣年輕,長了張滿懷希望的臉。其中一個是陸軍軍官的妻子,跟我一樣;一個是來自上海豪門,舉止文雅的女孩,她帶了少少的錢逃了出來;還有一個南京出身的女孩,她的頭髮是前所未見的黑。她來自一個低等家庭,但長得漂亮,為人親切,而且嫁得很好。跟她結婚的老頭死後,留給她富裕的生活。
「每週其中一人會主辦募款宴會,同時振奮各自的精神。主辦人必須準備特製點心,以帶來各式各樣的好運——銀元寶狀的餃子、象徵長壽的長米粉、象徵生子的煮花生,當然還會準備福橘,祈禱生活充實而甜美。
「我們用微薄的補貼為自己準備多麼精緻的食物!我們沒注意不部分餃子裡塞的都是黏稠的南瓜餡,橘子上有蟲蛀過的洞。我們吃得很少,不是不夠吃,是為了抗議我們不能多吃。當天早些時候,我們已經吃得夠飽了,我知道我們過著很少人負擔得起的奢侈生活。我們是幸運兒。
「填飽肚子後,我們會拿一個碗裝滿錢,放在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然後我們會圍坐在麻將桌旁。我的麻將桌來自我的家族,是一種很香的紅木。不是妳說的花梨木,是紅木(hong mu),一種很好的木頭,我找不到匹配的英文字。那張桌子加裝了厚厚一層桌墊,所以當我們把麻將牌倒到桌面開始洗牌時,只會聽見象牙製的牌互相撞擊的聲音。
「開始打牌後,大家都不會說話,除了碰牌或吃牌時會喊『碰!』或『吃!』。我們很認真的玩,除了贏得勝利,感受喜悅外,什麼也不想。但在打了十六圈後,我們會再次宴會,這次是為了慶祝我們的好運。然後我們會聊個通霄,懷念過去美好的時光,表達對未來美好的憧憬。
「噢,多精彩的故事!故事到處都是!我們都笑得要死。像是一隻公雞衝進屋子,盤踞在飯碗上尖叫,隔天牠就被安靜地裝在同一個碗裡!一個女孩分別為兩個愛上同一個男人的朋友寫情書。還有一個笨笨的外國女士聽見一旁的鞭炮聲昏倒在廁所裡。
「人們覺得在很多人餓到吃老鼠,或之後窮途末路,像那些窮人一樣翻垃圾找食物時,我們每週都辦宴會是不對的。其他人認為我們都被魔鬼附身了,即使我們自己也失去了好幾代家人時大肆慶祝。沒了家園和財產,與至親分開,丈夫和妻子、兄弟和姊妹、女兒和媽媽。哼!我們怎麼還笑得出來?
「不是說我們沒有心或瞎了,感覺不到痛苦。我們都很害怕,都有屬於自己的不幸。但絕望代表希望挽回早已失去的東西,或是使難以忍受的痛苦延長罷了。妳想花多少錢買到自己衣櫥裡那件最愛的暖大衣,與自己的父母一起燒死在屋裡?妳在腦海還能看見多久胳膊和腿從電話線垂掛下來,還有餓壞的狗在街上奔跑,嘴上叼著咬爛的人手晃來晃去?怎樣才算最糟,我們捫心自問,是要掛著河乎體統的憂鬱臉孔等死?還是選擇自身的快樂?
「所以我們決定辦宴會,假裝每天都在過新年。每一週我們都可將過去的不幸拋諸腦後,我們不允許任何不好的念頭出現,我們宴客、大笑、打牌、有輸有贏,分享最棒的故事。如此一來,我們每週都能祈求福氣,擁有福氣是我們唯一的喜悅,所以我們將這個小聚會命名為喜福會。」
我媽媽以前常以快活的語氣結束這個故事,吹噓她打牌的技術。「好幾次都是我贏,因為運氣太好,其他人都開玩笑說我學到了聰明竊賊的把戲。」她說:「我贏了好幾萬元,但我並不有錢,因為那時紙幣變得毫不值錢,連廁紙都比錢有價值。這讓我們笑得更厲害了,想到一千元紙鈔還不能拿來擦屁股。」
我一直以為母親的桂林故事只是中國的童話,因為結局總是在變。有時候她說她用毫無價值的一千元紙幣買了半杯的米,然後煮一鍋粥,用粥換了兩隻豬腳。那兩隻豬腳後來便成八顆蛋,蛋又變成六隻雞,故事總是一變再變。
後來有天晚上,我求她買一台電晶體收音機給我,她拒絕我後,我生了一個小時的悶氣,她對我說:「為什麼妳要覺得自己缺少從未有過的東西?」然後她就告訴我一個結局完全不同的故事。
「某天一大早,一名軍官來到我家。」她說:「叫我快去重慶找我丈夫,我知道他是要我逃離桂林。我知道日本人一來,軍官及其家人會面臨什麼處境。我該怎麼離開?沒有火車離開桂林,我那個來自南京的朋友對我很好,她賄賂了一個男人,弄來一輛原本是用來運煤的手推車。她答應要幫忙警告其他朋友。
「我把行李和兩個寶寶放到手推車上,在日本人進入桂林前四天,開始推著推車出發前去重慶。途中,我從身旁倉皇逃離的人口中得知大屠殺的事,太可怕了。直到最後,國民黨仍堅持桂林是安全的,受到中國軍隊保護。但當天稍晚,桂林的街上撒滿報紙,報導國民黨的勝利,但在這些報紙上卻躺了一排排的人,彷彿砧板上的鮮魚——男人、女人和幼童,這些人從未失去過希望,卻葬送了性命。聽見這個消息後,我腳步越來越快,不斷問自己:他們是太笨?還是太勇敢?
「我往重慶的方向推著推車,直到車輪裂開為止。我扔掉了那張漂亮的紅木麻將桌,那時候我內心已麻木到哭不出來。我把圍巾用揹帶綁在身上,兩個寶寶各靠著我一邊肩膀;一手抓著一個包包,一邊放衣服,一邊放食物,拿著這些東西讓我雙手出現深刻的皺痕。而在我雙手開始滲出血絲,變得濕滑抓不住東西後,我終於把兩個包先後扔下。
「沿途,我看到其他人也做了同樣的事,逐漸放棄希望。就像鋪著珠寶的道路,一路上不斷增長價值。上等的織物和書籍、古董畫作和木匠工具,直到大家可看見一籠小鴨渴得叫不出聲來,再後來,銀甕躺在路上,沒人有力氣為了未來的生活去撿的地步。我到重慶的時候,除了穿在身上的三件花俏的絲綢洋裝,失去了一切。」
「妳說『一切』是什麼意思?」我最後抽了口氣。我很震驚得發現這整段故事一直都是真實發生過的。「那些寶寶呢?」
她不假思索,只是簡單的用故事已經說完了的語氣回答:「妳爸不是我第一任丈夫,妳也不是那兩個寶寶其中之一。」
當我抵達徐家,今晚喜福會的聚會地點時,第一個見到的人是我父親。「她來了!從來不會準時!」他宣佈道,而這是事實。其他人都到了,七名六、七十歲的家族朋友。他們抬頭對總是遲到的我微笑,三十六歲了仍是個孩子。
我渾身發著抖,試著克制激動的心情。上次我看見他們是在葬禮的時候。我陷入崩潰,整個人哭得抽抽搭搭的,他們現在一定想我這樣的人該如何接替我母親的位置。一個朋友曾說我跟我媽很像,我們有一樣纖細的手勢、少女般的笑聲和斜眼看人的習慣。當我害羞地跟媽媽說了這件事後,她似乎受到侮辱,並說道:「妳根本一點也不瞭解我!又怎麼會像我?」她說得沒錯,我怎麼能在喜福會充當我媽的角色呢?
「叔叔、阿姨。」我重複地像每個人點頭打招呼。我一直稱這些老一輩的家族朋友叔叔、阿姨,接著走過去站到了我爸旁邊。
他正欣賞鍾家最近中國行的照片。「妳看。」他禮貌地表示,指著鍾家跟的旅行團站在寬板台階上拍的照片。這張照片中沒有任何東西可證明是在中國而非舊金山拍的,或是其他城市。但反正我爸好像也不是在看照片,就好像每件事對他來說都大同小異,沒什麼特別的。他一直都有禮得恰到好處,任何事都無動於衷,但形容一個人無動於衷是因為他看不見任何差異的中文是怎麼說的?這就是我覺得母親的死對他打擊很大的原因。
「妳看那張。」他說,指著另一張平淡無奇的照片。
徐家的房子滿是油膩的氣味,感覺空氣發沉。廚房太小,卻煮了太多中國菜,太多菜餚的香味被一層看不見薄薄的油脂包覆住。我記得我媽以前去別人家和餐廳時會皺著鼻頭,大聲地說:「我都可看到也感覺鼻子黏黏的。」
我好多年不曾拜訪徐家了,但客廳就跟我記憶中的一模一樣。當安梅姨和喬治叔叔(Uncle George)二十五年前從中國城搬到日落區(Sunset district)後,他們買了新傢俱。傢俱全都在,在泛黃的塑膠布下看起來幾乎跟新的一樣。同樣一張綠松石色的粗花呢半圓沙發;硬楓木材質的殖民風小茶几;一盞有裂紋的仿冒瓷燈,只有廣東銀行(Bank of Canton)贈送的日曆掛軸每年都會更換。
我記得這些東西,是因為我們還小的時候,只有蓋著透明塑膠布,安梅姨才讓我們摸她的新傢俱。每到喜福會的晚間聚會,我父母會把我帶到徐家。自從我去作客以來,不得不照顧其他年幼的孩子,太多小孩了,似乎總有人撞到桌腳嚎啕大哭。
「妳要負責。」我媽說,意思是如果有東西弄倒了、燒起來、不見、壞掉或弄髒我就慘了。不管誰做的,我都要負責。她和安梅姨會穿上好笑的中式洋裝,有僵硬的立領,胸前還有以絲線刺繡的花朵盛開的圖案。我心想,這些衣服對真正的中國人太過花俏,穿在美國人身上又太詭異。那段日子裡,在我母親告訴我她的桂林故事,我想像中的福喜會是可恥的中國習俗。像是三K黨(Ku Klux Klan)的秘密集會,或是電視上出現的印地安人在戰前跳的咚咚舞(tom-tom dances)。
21*14.8*1.6
25 開
三十週年新版序
第一章 千里鵝毛
吳菁妹:喜福會
許安梅:傷疤
鍾林冬:紅蠟燭
瑩影.聖克萊爾:月亮娘娘
第二章 二十六道鬼門關
薇芙莉.鍾:遊戲規則
琳娜.聖克萊爾:隔牆的聲音
蘿絲.許.喬丹:一半一半
吳菁妹:兩種
第三章 美國翻譯
琳娜.聖克萊爾:飯粒丈夫
薇芙莉.鍾:四方
蘿絲.許.喬丹:缺木
吳菁妹:最佳品質
第四章 王母娘娘
許安梅:喜鵲
瑩影.聖克萊爾:潛伏樹林間
鍾林冬:雙面
吳菁妹:兩張機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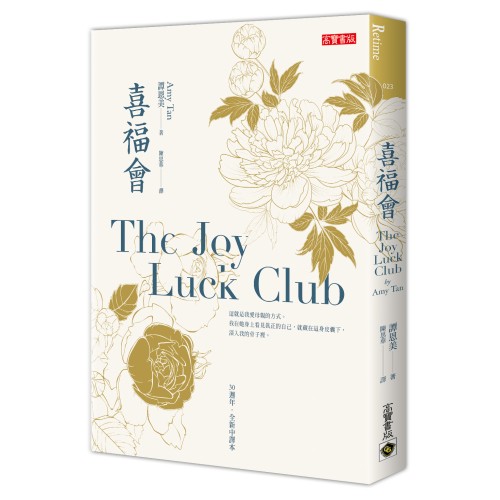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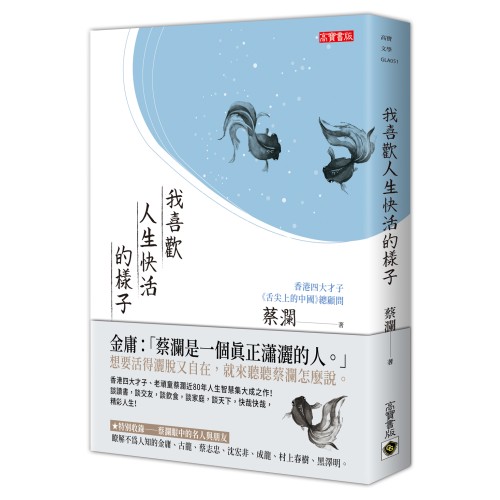
_立體書+贈品-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