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被封鎖的城市,被封鎖的消息,被封鎖的犯罪現場☆
☆英、美亞馬遜網站與美國最大書評網Goodreads上超高評價推薦☆
這個具有前瞻性的驚悚故事寫於15年前,被束之高閣、從未出版,現在卻如此貼近時事,不可避免地具有強烈既視感。
他們說,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會感染流感。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會死亡。
倫敦,這座城市因致命的病毒已經使數千名受害者喪生,沒有人能倖免。而病毒大流行處於封鎖狀態的倫敦,醫院和急救服務不堪重負,暴力和內亂正在沸騰。
傑克·麥克尼爾(Jack MacNeil)的職業生涯陷入一片廢墟,他的婚姻結束了,他的家人被病毒感染。背後有險惡的人正在追蹤他的一舉一動,準備再次殺害以掩蓋事實。究竟誰將先阻止他,病毒還是殺手?
各界推薦
彼得.梅……是一位跟上時事的犯罪小說家,《封鎖》一書帶有預示性,讓人惴惴不安。——《衛報》(The Guardian)
他筆下的病毒比新冠病毒更加致命,但他對於被圍困城市景象的描繪及對疾病傳播蔓延的見解……驚人的有先見之明。——《觀察家報》(The Observer)
彼得.梅所描述因為全球大流行的強大病毒而進行封城的倫敦,如今只能說再真實不過了……,斥著細節,讓人感到不舒服,但又令人無法控制地閱讀下去。——《每日郵報》(Daily Mail)
《封鎖》感覺恰如其分,每一頁都充斥著存在的恐懼。——尼克.杜爾登(Nick Duerden),《iPaper》
非常切合主題。——《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
駭人且扣人心弦的驚悚小說。——《S雜誌》( S Magazine )
以一個毀滅性傳染病爆發為背景的犯罪小說是什麼樣子?彼得.梅費盡心思提供讀者一個嚴峻而合理的答案。——《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序章
女孩的尖叫在黑暗中迴盪,顫抖的聲音從因恐懼而緊縮的喉間擠出來,但凡任何有同情心的人聽了都會汗毛直豎;但這幢古老宅邸四周厚牆圍繞,讓整棟房子籠罩在恐怖的氛圍中,確保不會有人聽見她的呼救。
他在黑暗中低聲唾罵,感到很氣惱。她聽見他走上樓梯,很清楚他想傷害她,這個她所熟悉、信任甚至愛過的男人。不解的念頭壓得她喘不過氣來,這怎麼可能? 她還記得在她漫長折磨的生病期間,他把手貼在她發燙的額間傳來冰涼的觸感,眼中流露出憐憫;現在卻冒著熊熊怒火,充滿惡意。
她屏住呼吸,男人又走上另一段台階。他以為她跑到了頂樓,她則在溜出書房時,看到樓梯上他的影子正往閣樓上去。她隨即轉身匆匆下樓,小小的腳丫踩在厚地毯上,進到從彩色玻璃窗投射到門廳地板上的光裡。她用手拼命拉著門把,但門上鎖了,根本無處可逃。她聽見樓上傳來男人的怒吼,頓時渾身僵硬。他發現跟丟她了。她有些猶疑,通往地下室的台階位於樓梯下方的廁所,但她知道一旦下去就是死路一條;剩下就只有一條連到外面巷子的老舊輸煤管,即使她身材嬌小,也無法鑽過管道。
男人怒氣沖沖地下樓來,每走一步房子就跟著震動。她驚慌地轉身,發現面前站了一個小女孩:身穿白色睡袍的亡靈,留著率性的黑色短髮,一雙杏眼又大又黑,臉色慘白。女孩恐懼的目光像是刀刃般向她刺來,她才意識到她閃避的正是自己的倒影,一張驚恐扭曲的臉孔,讓她認不出來。
「喬伊!」她聽見男人的吼叫從樓梯間傳來,突然想起幾個月前初次帶他們參觀這棟房子的女人,和位於房屋前側那間寬敞飯廳牆上的假鑲板;他們從未在那裡用過餐,整個房間一直處於悶熱昏暗的環境中,日光和燈光交替從百葉窗周圍的縫隙透進來。那名房仲曾把一張小茶几移開,卸下牆板露出後方的門。她握著圓形門把,打開那扇刷著白漆的舊門進入一個更黑的地方。那是一間小小濕冷、帶有霉味的磚房,過去一家六口曾瑟縮在這個黑暗空間躲避空襲。
喬伊不知道那位女士口中的「閃電戰」是什麼意思,但她曾聽說德國的轟炸機隊炸完倫敦後,再次繞到南邊,將機上未用完的彈藥扔向這個不幸的自治市鎮。當警報響起時,人們紛紛抱頭鼠竄,躲進家中骯髒的磚房豎耳傾聽,在黑暗中等待並祈禱。喬伊又聽見男人大吼她的名字,正如半個多世紀前的警報聲一樣,使她慌慌張張地跑進客廳。
她匆匆把茶几推到一旁,摸索著牆面,扳開深藍色鑲板上的拴扣;鑲板很重,她用自己的小手使勁將板子撬開,而後聽見男人踏到二樓走廊,走進上方主臥室的聲音。她把鑲板傾向一邊推開門,門後方一片漆黑,濕冷的空氣將她團團包住。她踏了進去,接著把鑲板挪回原位。由於從裡面沒辦法把鑲板扣緊,她只能祈禱他不會注意。一關上門便沒了光線,她蹲下身,環臂抱住自己取暖。這裡又冷又黑,什麼都做不了,無路可逃。她想不通這個空間要怎麼擠進六個人,也難以想像聽見四處投彈的聲音,猜想下一個會不會是自己是什麼感受。但她不需要想像也能在腦海描繪出現在樓梯上的男人,或光照在他帶著的那把刀的畫面。位於廣東的那家孤兒院是段遙遠的記憶,那是她的童年,屬於別人的人生。才六個月,一切都變了,但感覺像是過了很久,上一段人生不過是夢的幻影。
她呼吸急促,似乎異常清晰,卻能聽見男人走入客廳的聲音:踩在實木複合地板沉重的腳步聲,和他再次大吼她名字所蘊含的憤怒,接著安靜下來。這陣靜默似乎從一會兒延伸為數小時。她盡可能屏住呼吸,因為她確定男人肯定會聽到她的呼吸聲。上頭仍然沒有任何聲響,然後她在聽見門外鑲板刮過牆面的聲音時倒抽一口氣。
門把轉動,她在門慢慢打開時,將背緊貼著牆面。門後大廳流進的燈光襯出男人的身影,透過同樣的光線,她看見自己的呼吸在冷空氣中凝結。男人慢慢蹲下身,把手伸向她。她看不見他的臉,卻能聽到他在笑。
「到爸爸這兒來。」他輕聲說。
第一章(節錄)
I
大主教公園一面旗幟襯著夜色垂掛在建有垛牆的塔樓上方,大主教正停留暫住宮殿中,但由於推土機短暫休息六個小時後,凌晨五點便開始動工,他似乎不大可能還在熟睡。開放這座公園,讓整個自治市鎮使用的前人大概也無法安息。
弧光燈照亮施工現場,過去孩童玩耍的土地遭工程車履帶輾過變得濕軟,迴盪在空氣中細小的回聲被機器的轟鳴聲淹沒;足球和籃球場的欄杆被挖開扔到一旁;鞦韆殘骸和攀爬架堆在公園西側等著拆除的廢棄大樓旁;原本打算改建咖啡館的老舊廁所區已經被拆除。時間急迫,大量人力被指派完成這項任務。十八小時輪班一次,沒人有怨言,因為薪水優渥,但現在也無處可花。
一群身穿橘色連身工作服、戴著安全帽和白口罩的人在燈下四處走動,沒人交談。每個人都自顧自地做事,與其他人保持距離。他們透過口罩乾淨的布料抽煙,留下沾到尼古丁的圓形汙漬,還有一個持續燃燒的火盆銷毀抽完的菸頭。感染很容易散播開來。
昨天工人為了建造地基挖了洞,今天便來了好幾輛水泥車灌入混凝土。一台大型吊車已抵達現場,準備吊起鋼樑移動到位。緊急委員會前一天下午派了支代表團從西敏區走一小段距離到現場,喜憂參半地觀看他們迫於無奈批准的拆除行動。雖然臉上戴著白色布口罩,卻遮不住他們焦慮的眼神。他們一樣默默看著工程進行。
此時,突然有個聲音壓過攪拌水泥和挖土機的噪聲,一個人影在黑暗中舉手叫停。他身材瘦長,站在西北角一個大坑旁。水泥溜槽大幅度擺動,搖晃地停了下來,下一秒灰色汙泥就要噴湧而出。男人蹲在坑口看向下方一片漆黑。「下面有東西。」他喊道,工頭氣憤地大步踩過泥濘向他走去。
「拜託,我們沒時間做這種事了!」他朝操作水泥車的人揮了下戴著厚手套的手。「快!」
「不,等一下。」身材瘦長的男人跳到坑裡,不見了蹤影。
工頭抬頭仰望天空。「天啊,來點燈照一下這裡。」
架好燈架後,隨著光斜斜打下來,一群人圍在坑口四周。男人瘦長的身影蹲在某個又小又黑的東西上方。他抬頭望著那圈往下盯著他的臉,用手遮住刺眼的光線。「是個他媽的提袋,」他說:「皮革提袋,某個白癡以為我們挖這個洞是要給他丟垃圾。」
「拜託你快上來,」工頭大喊:「工程不能有任何延誤。」
「裡面裝什麼?」有人喊道。
男人用袖子抹掉額頭的汗水,脫掉一邊手套拉開提袋拉鍊。所有人都俯下身想親眼瞧瞧,然後他像是摸到帶電的電線似的往後一跳。「媽呀!」
「是什麼?」
他們可看到某個白色物體在光線照射下閃閃發亮。男人抬起頭,呼吸急促,喘著粗氣,原本因為睡眠不足而蒼白的臉更是毫無血色。「我的天啊!」
「到底是什麼?」工頭開始失去耐性。
坑裡的男人小心翼翼地再次靠上去。「是骨頭,」他聲音低沉,卻能讓所有人聽到。「人骨。」
「你怎麼知道是人骨?」其中一人問,他的聲音異常大聲。
「因為有一顆他媽的人類頭骨盯著我看,」男人仰起自己的頭,皮膚似乎繃得緊緊的。
「但很小,對大人來說太小了,這肯定是小孩的頭骨。」
II
麥克尼爾正身處異地,一猛然驚覺自己已經好幾個月沒去上班。他怎麼能忘記? 但他知道他以前就幹過這種事,因為他有段模糊的記憶。噢,該死,他要怎麼解釋? 要怎麼跟他們說明他去了哪裡或為什麼? 天啊,他覺得很難受。
他聽見電話在響,知道是他們打過來的。他不想接。他能說什麼? 他們一直都有付他薪水,他卻連出現都不願意;其他人鐵定不得不幫他掩護,替他輪值,他們會很生氣、會指責他。電話仍響個不停,但他就是不想接。「閉嘴!」他對電話大吼,電話毫無反應,每一聲響鈴都宛如利刃刺向他的胸口,會一直持續到他接起電話。他滿頭大汗,感覺有什麼東西黏在身上,越使勁掙扎就越擺脫不了。他翻來覆去,最後醒了過來,大口喘著氣,瞪大眼睛,驚恐地盯著天花板,剪得短短的頭髮濡濕地貼在枕頭上。電子顯示的數字「06:57」朝著日光升起的方向延伸。他只從那個家裡帶走這個尚恩送他的禮物,一個會將紅外線數字投射到天花板上的鬧鐘。
麥克尼爾把自己從被汗浸濕的被褥中解救出來,雙腳晃下床坐了起來。冷冽的空氣朝他襲來。起來! 電話仍鈴聲大作,就像他夢到的一樣,他知道響鈴不會停止。他手伸向床頭櫃拿起話筒,動了動乾涸的嘴唇。「喂?」
「你最好醒了,麥可尼爾。」
麥可尼爾動了下黏在上顎的舌頭,口腔隨即散發出威士忌的酸味。他揉了揉眼睛抹去眼屎。「我還有十二個小時才當值。」
「情況有變,現在你要值兩班。我想既然這是你最後一天上班,應該撐得過去,我又有兩個人不行了。」
「該死。」
「的確該死,有個傢伙在我們後院丟了東西,我沒別人可用了。」
麥克尼爾抬頭往後仰,疲憊地看向上方那顆大時鐘。反正他也不知道接下來的十二小時要做什麼,他很難在白天入睡。「怎麼回事?」
「骨頭。一群工人在大主教公園施工現場的一個坑底發現到的。」
「聽起來他們需要的是考古學家,不是警察。」
「骨頭被裝在一個皮革提袋裡,而且昨天還不在那裡。」
「啊。」
「你最好直接跑一趟。政府相關部門因為不得不停止施工一直抗議,趕緊結案好嗎? 我不想要這有的沒的麻煩。」
電話那頭傳來咔的一聲,嚇得麥克尼爾縮起脖子。萊恩掛斷了電話。
麥克尼爾穿過走道到盥洗室,邊刷牙邊盯著自己茫然的倒影。其他人的牙刷全擠在一個混濁的牙刷杯裡,他所有私人物品都放在自己房間,盥洗室的用品一概不碰,甚至在使用水龍頭前都要先消毒擦過一遍。他得刮一下鬍子,再睡幾個小時或許有助於消除黑眼圈,卻沒辦法改善過去幾個月來造成的痕跡。戴口罩在他年近不惑的臉上留下烙印,他可不想一直維持這個形象。
他在用刮鬍刀刮鬍子時,聽見隔壁有人醒來的聲音,是那個汽車銷售員。麥克尼爾第一次到這裡租房時,住在一樓的房東便帶他認識同樣住在這裡的房客:一名離婚的醫生,目前禁止開診,他通常能很快為大多數疾病提供藥方,是個很可靠的鄰居,尤其在最近這段日子。一名汽車銷售員,房東認為他是同性戀,但還沒決定接受自己的性向。兩名鐵路工人工會的職員,只是現在不叫這個名字,他也不記得改成什麼了,他們一人來自曼徹斯特,另一人來自里茲,兩人任職於工會設於倫敦的執行委員會,這個工會長期在巴勒別克路上執行業務。整棟屋子只有一個女房客,她身上帶著異味,看起來就像行屍走肉,房東很確定她在嗑藥,但她總是按時付房租,所以他也沒資格對她說三道四。
這群怪人八竿子打不著,住在社會邊緣,處於半死不活的模糊地帶,只是存在而已。他第一天搬進來時,麥克尼爾感覺自己就像個局外人,只是來看看的旁觀者。他不屬於這裡,也不會留下來—這真的只是五個月前的事嗎?住在這裡的所有人肯定都這麼想過,現在麥克尼爾就像他們一樣,看不見出路。他不再是站在外面觀望,而是從裡面向外看。
選擇這個地區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可以帶著尚恩搬進這裡。這裡並非貧民窟,仍然給人一種沒落的貴族氛圍。馬路的盡頭就是海布里綠地,他和尚恩可以去那裡踢球、遛狗—如果他們有養的話。離海布里綠地不遠有一座游泳池,房東說以前那裡是戶外空間,但不那麼耐操的後代建了圍牆,又蓋了屋頂,是另一個他和尚恩可—要怎麼說?—享受美好時光的去處。而且麥克尼爾還覺得,他可以幫他們倆買季票去酋長球場看兵工廠足球俱樂部比賽。
但尚恩的媽媽拒絕讓他跨越市區到伊斯林頓自治市來。太危險了,她說,等緊急狀態解除再說吧。
麥克尼爾穿上外套,豎起衣領。他的西裝需要燙一下,白襯衫領口的位置有些磨損;最上面那顆鈕扣掉了,為了遮住,他把領帶繫到最緊。戴上手套後,他匆匆下到一樓的窄廊。有段時間,差不多就在一個月前,房東會把頭探出門外向他道早,但現在兩人都不交談,因為太害怕傳染。
III
麥克尼爾一關上門,便聽到樓上電話在響。他不想再跟萊恩通話,所以他很快掏出手機關機。
坐進駕駛座時,他感覺車裡空氣冷冰冰的,雖然沒有結霜,水氣卻凝結在擋風玻璃蒙上一層霧。他打開風扇,將車拐進卡拉布里亞路。收音機放著去年的精選曲目,最近兩個月完全沒有人出新專輯。音樂一首接一首的放,麥可尼爾很高興沒有那些清晨時段常會出現的愚蠢、擾人的DJ。他錯過了七點三十分的新聞廣播。
老樣子,他通往市區的路線取決於軍方的檢查哨。某些特定地區禁止進入,連他也不例外。有些界線需要特殊許可才能越過。他驅車向南前往本頓維爾,沿著本頓維爾路往西轉入尤斯頓路。現在將近七點四十五分,黯淡的光線穿過低矮的雲層在空中蔓延開來,掠過遠方摩天大樓頂部。以往計程車、公車和上下班的人會阻塞這座城市的動脈,就像膽固醇一樣。麥克尼爾仍不習慣街上空蕩蕩的,在清晨的曙光中有種詭譎的靜謐。經過偶然碰見的部隊車,戴著防毒面罩和護目鏡的軍人在卡其色的帆布帳下注視外頭,宛如出現在《星際大戰》電影中戴著面罩的軍人,抱著他們常常被迫使用的步槍。
現在天已經亮了,有少少獲得通行許可的私人和商業車進入這座城市的指定區域,透過相機與衛星進行追蹤。因為市中心發生過很多搶劫事件,所以管制最為嚴格。政府用舊的都市擁擠收費設施監管所有進出車輛。麥克尼爾沿著北方界線前進,經過空無一人的尤斯頓車站,才轉往南邊的托登罕宮路,被一個攝像鏡頭拍下車牌,立即傳送到中央電腦。沒有許可,他可能會在幾分鐘內被攔下來。
這座城市的購物街宛如戰場。窗戶未被砸破的商店已釘上木板,被燒毀的贓車骨架在路邊冒煙,這個曾經代表文明社會的殘骸就散佈在滿是狼藉的街上,又是一晚暴力事件的殘留。位於地鐵托登罕宮路站對面的自治領劇院成了燒毀焦黑的軀殼,只要下雨,空氣中就會瀰漫最後上映的那片《推銷員之死》的影帶燒焦的氣味。牛津街上那家麥當勞同樣遭到燒毀,火烤漢堡煮過頭了。店名為「和諧」的情趣用品店被闖空門的次數多到店主不再浪費時間釘上木板,一身黑色皮衣的性感美女在麥克尼爾開車經過時挑逗地朝他噘唇。
再往南走,聖馬丁劇院的霓虹燈全被砸碎,從牆上扯了下來,看起來顯得悲涼。《捕鼠器》也終於中斷其空前絕後的長時間公演紀錄。
他在劍橋圓環的檢查哨前停下來。如今他也該習慣這種事了,但被六把半自動步槍指著頭總讓他感到不太自在。一名臉色陰鬱的軍人戴著面罩,虎視眈眈地盯著他,與他保持一段距離,伸出戴上乳膠手套的手接過文件。他很快地把文件遞還回去,急著擺脫那些紙,彷彿受到了污染—當然這是很有可能的。
麥克尼爾沿著查令十字路行駛,穿過特拉法加廣場進入白廳。這裡有更多活動的跡象,政府行政機關仍勉強運作,試圖解決社會崩解的問題。戴著口罩的男女在權力中心進進出出,跟首都大多數居民一樣籠罩著慘淡的絕望。
當他駛近河畔時,看見黑色的濃煙從巴特西發電站的四根煙囪升入雲幕低垂的晨空。面對大自然難以想像的無情反撲,這是證明人類無助更有力的象徵。現在死了多少人? 五十萬?六十萬? 還是更多? 沒人相信這些數字,因為根本無從驗證。但即使在最樂觀的估計下,政府給出的數字仍讓人難以想像。
八點的新聞正在報導整晚不斷播放的新聞,但這是麥克尼爾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使他震驚不已。午夜後不久,聖湯瑪士醫院的醫生宣布總理死亡的消息。他的兩名小孩早已病故,妻子仍在病危中。總理病情嚴重並非秘密,但倘若這個國家的最高元首如此輕易就被打倒,那他們這些百姓還有什麼希望呢?
14.8*21cm
25 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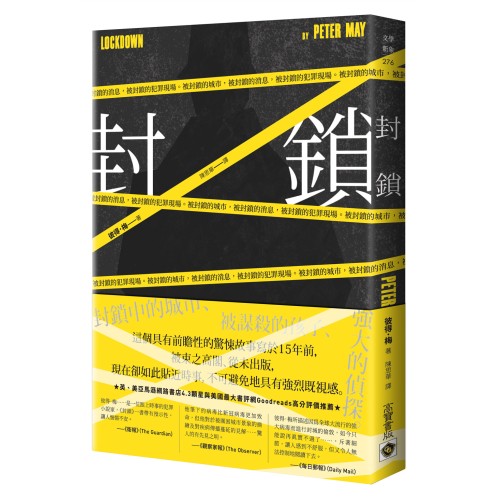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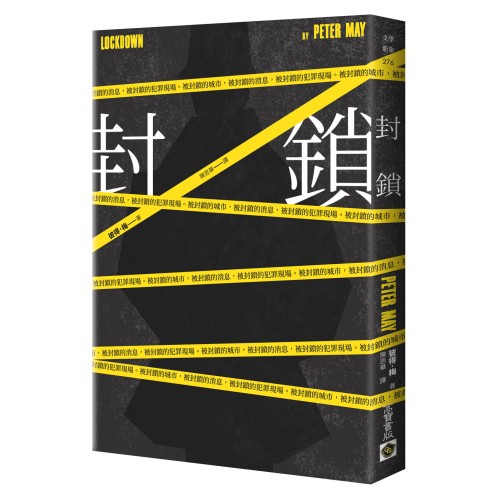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作者印簽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500x5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