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我們都活在自己創造的現實裡,等待真相揭露的那一天。
★入選阿嘉莎獎年度最佳小說!
★《書單》星級書評
★亞馬遜編輯精選最佳懸疑驚悚小說
★《Criminal Element》年度最佳驚悚小說
★《REAL SIMPLE》年度最佳驚悚小說
★《Book Bub》年度最佳夏季驚悚小說
★《POPSUGAR》年度最佳夏季驚悚小說
★《CrimeReads》年度最值得期待的驚悚小說
★《紐約郵報》年度最佳夏季驚悚小說
「塑造懸疑謎團的大師」、「天賦異稟的說書人」――美國《國家評論》
「精采至極,一流的心理懸疑之作」――《書單》星級選書
德克斯和蘇菲死了,是梅瑟親手害死的。警方說是意外,法律說她無罪,朋友也說不是她的錯,那麼,該是誰的錯呢?梅瑟每天在鏡子上寫下數字,贖罪般計算著失去丈夫與女兒的日子,直到另一個小女孩出現,她占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她與裝著她殘餘屍體的綠色垃圾袋。
艾許琳從沒想過有一天會被自己的母親指控謀殺。那個裝在綠色垃圾袋裡的屍體真的是她女兒嗎?真的是她的泰莎嗎?她還來不及消化這個噩耗,就被關進監牢等候審判。全世界的人都認為她有罪,就算她被無罪開釋,也不會有人相信她吧,包括眼前這個說要為她寫書平反的女人。
「告訴我真相,艾許琳,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妳真的想知道嗎?梅瑟,那如果我說妳的女兒不是死於意外呢?」
【各界盛讚】
令人著迷!《無罪之罪》更勝漢克.菲莉琵.萊恩以往的作品!不僅有性命攸關的緊張驚悚,令人不安的盟友,還有貓捉老鼠的致命遊戲。
――《活著告訴你》犯罪小說暢銷作家麗莎.嘉德納(Lisa Gardner)
神作!我讀過最驚悚的小說之一。
――《懸疑雜誌》(Suspense Magazine),安德魯.古里(Andrew Gulli)
文字優美,劇情巧妙,《無罪之罪》緊抓著讀者的心,讓人忍不住一口氣讀到最後。萊恩又交出一部傑出的心理懸疑大作。
――《當他不愛我》懸疑小說作家溫蒂.沃克(Wendy Walker)
引人入勝……《無罪之罪》是一本緊張曲折的心理驚悚之作,探討「真實」的各種面相。顫慄、懸疑,讓人目不轉睛,直到最後仍不斷揣想究竟誰可以信任。
――驚悚小說作家梅根.米蘭達(Megan Miranda)
入時、懸疑、巧妙……讓人愛不釋手。這本傑出的小說,精心結合了引人深思的故事情節和刻劃入微的人物角色。讀完之後仍一直盤旋在我的腦海。
――(已歇業)阿嘉莎書店(Aunt Agatha's Bookshop)主人,羅賓.安格紐(Robin Agnew)
讀到無法自拔!緊張的氛圍、精心刻劃的人物,讓你又愛又恨。這本曲折的心理驚悚小說,不僅描繪法庭上的高潮起伏,還有我自以為可破解、結果卻完全誤解的巧妙謎團。不可否認,這是漢克.菲莉琵.萊恩截至目前為止的巔峰之作,我等不及要推薦給書店的客人了。
――獨立書店Mystery to Me主人,瓊安.伯格(Joanne Berg)
Part 1
即便回到昨天也無濟於事,因為那時的我與此刻並不相同。
──路易斯.卡羅,《愛莉絲夢遊仙境》作者
我用手指在浴室鏡面上留下字跡,劃過淋浴後瀰漫的霧氣。今天早上的數字是四二二。
一場事故摧毀了我的家庭,將德克斯和蘇菲從我身邊奪走,至今已經過了四百四十二天。我寫下數字的同時,蒸氣逐漸散去,字跡化為水珠,如同眼淚一般滑下,終至消失。
我願意付出一切,一切;我願意去做任何事。看著鏡中的倒影,一股深切的渴望給了我重重一擊,但無論我多渴望,都早已無濟於事。人們終日祈禱:如果你答應,我保證會戒酒、再也不超速駕駛,我可以做到任何事。只要你答應,我一定會當個好女兒、當個好丈夫、我會當個全心奉獻的妻子。
讓我的願望成真,我可以做……任何事。
然後我們妥協、周旋,試圖和上天交易。我們通常得以獲得所求。
但接著,上天會訕笑我們,最終留下我們獨自一人,只能試著與自己妥協。
1.
你認識我嗎?我當然看過那些廣告招牌、海報、全彩合成畫像刊登在各大電視節目和報紙上,大概全波士頓的人都看過了。「可憐的小女孩。」大家都這麼說,「她是誰?一定有人很想念她。」
有的人看到畫像之後,不由得將身旁的孩子拉近自己,低聲警告他們,又或者是在超商購物時,將一隻手警戒地放在身邊的娃娃車上。
「梅瑟,妳可以嗎?」凱薩琳語帶關切,在電話另一頭的聲音變得輕柔了一些,「妳得重新開始工作。」
我沉默不語好一陣子,一直出神地想著「波士頓寶寶」。
「妳還好嗎?」她追問。
「嗯,我沒事。」凱薩琳想要我寫下這可怕罪行的真實內幕。我癱坐在書房的椅子上。我可以嗎?老實說,我不確定。
「這本書馬上就會變成暢銷書,親愛的,可以讓妳重回戰場。」凱薩琳再接再厲,試圖說服我。
「孩子在波士頓港被殺害後棄屍,接著母親因謀殺罪遭到起訴。抱歉,我真糟糕,我知道這太趕了,但妳是唯一一個能寫這個故事的作家。我可以告訴他們妳願意接嗎?」
幸好她看不見我臉上的表情。一樁悲慘的弒童案,卻是這陣子對我來說最好的一件事了,雖然世人可能無法接受這種想法。自從周遭的人一個個離去,我就很少跟人接觸,也不再回覆任何人的來電,所以有好幾個月都沒有收到以前編輯的來信,現在,工作機會終於來了。
凱薩琳.克拉夫向我解釋,我所要做的,就只有從明天開始,使用與電視臺一樣的轉播訊號全程觀看開庭過程,然後寫一本關於波士頓寶寶謀殺案的「話題書」。「人們當然可以從電視上看到,」她說,「但萬一某個白痴製作人把報導搞得很無聊呢?或者萬一他們刪減了某些片段,只為了播一些小狗被困在牆上的新聞,或一些網路假消息呢?我們不能讓他們來決定要公開哪些資訊。所以,讓妳來全面報導才能萬無一失。我本來想要幫妳在法庭上安排一個座位,親愛的,但遲了一步。」
幸好沒座位,但我沒說出來。我怎能面對這麼多人?凱薩琳接著向我開出預付一萬五千美金的條件,在判決結束且書籍上市之後,再加碼一萬五千塊,未來還能拿到高額版稅。我確實需要錢。
「除非她無罪,」凱薩琳繼續說,語調變得十足輕蔑,「但這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艾許琳.布萊恩被定罪,妳就會成為『暢銷作家梅瑟.漢尼西』,我保證。」
如果是那樣就太好了,更重要的是,這本書也許會成為我每天早上起床的動力,雖然我沒向凱薩琳承認這一點。
「殺人犯從來不會是媽媽,對吧?」她再加把勁,說得好像她最懂,「有可能是媽媽的男友,或爸爸。但媽媽本人?那根本就是瘋了。」
確實,從來不會是媽媽,若是的話,可就有好戲看了。
這個案子正是如此,確實就是非常瘋狂。凱薩琳現在人在她後灣區的辦公室,而我則在自己
郊區住宅的小書房裡,但我能想像這位前編輯的表情。她說的和我在電視節目上聽到的一樣,而大排長龍買咖啡的人群也是如此議論。人們互相問道:「到底是怎樣可怕的母親會殺死自己兩歲的孩子?」
「她……」我在腦中搜索著足夠可怕的形容詞。這個母親一定有罪。我迅速地讀完報章雜誌上的每一篇文章,看了所有相關的電視新聞和專題報導,甚至連俄亥俄州電視臺的網路新聞都看了。
這些報導全都寫滿了令人心碎又駭人的細節,描述這個小女孩如何失蹤,而後屍體又如何被尋獲。
起初,我無法停止為那死去的可憐孩子哭泣,接著我對身為母親的痛苦感同身受,流下更多眼淚。
用別人的悲傷來填滿自己的思緒對我來說輕鬆多了,更希望能藉此取代自己的悲傷。雖然沒有很成功,但總比空虛好上許多。
泰莎.妮可的身分終於確認時,我曾考慮打電話給艾許琳,可笑地想以同樣身為母親的身分來安慰她,我們都一樣沉浸在悲痛之中,哀悼珍貴的寶貝女兒。現在連想起這件事都讓我反胃。她怎能如此欺騙我、欺騙所有人?在她被捕的新聞播出之後,我簡直想親手殺了她。
肯定沒有陪審團會因此定我的罪。
「梅瑟?妳還在嗎?」凱薩琳完全處於開會模式,好像我們還在一起工作,每天都會說上許多話似的,「試試看吧,親愛的,就答應吧,已經夠久了,妳得重新開始工作;妳得做點什麼。」
做點什麼?要做什麼?我差點朝她大吼。但她是出於好意,她一直陪伴著我度過那些日落後黑暗籠罩的日子。凱薩琳盡可能理解我,比其他人所能理解的都還要多。我把自己的悲傷發洩在她身上並不公平,她說得對嗎?真的有任何事情是我能做的嗎?
或許……為了蘇菲?還有德克斯;或許就當作是彌補他們的遭遇,並接受我是活下來的那一
個。我不是在自欺欺人,我永遠也做不到這一點,但此刻,我能感覺到德克斯,彷彿他正催促我去做。用我的文字去糾正錯誤,去伸張正義,就像他過去所做的那樣。我彷彿聽見他的聲音對我說:更重要的是,妳能以此紀念蘇菲。
對,德克斯說得對。沒錯,我會去做,為「波士頓寶寶」復仇。然後我會暗自將這本書獻給蘇菲,獻給每一個被不公平帶離這世上的小女孩。我越想著這一點,就越明白自己做得到。我渴望去做,我的身體、心靈和情感都想要去做這件事。
更何況,寫一本書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選項。
也許我會把房子燒了。在凱薩琳打電話來的幾天前,我真的曾經大聲這麼說,只是沒有人聽見。
我彷彿能看見火焰;我想像著育兒家具上那些粉紅色花蕾和華麗的滾邊,全都被大火燻得焦
黑,還有德克斯穿上法庭的時髦西裝、蘇菲的雛菊圖案睡衣和絨毛玩偶、婚禮照片和牙刷,還有……
我們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林斯戴爾消防隊會前來與地獄般的烈焰和嗆人的濃煙搏鬥,試圖從大火中拯救漢尼西一家人曾經存在的證據,卻澈底失敗了,那時我會有什麼感受呢?我恐怕沒辦法活著知道了。
這就是重點。
「梅瑟?」凱薩琳打斷我的思緒。
我將凱薩琳的來電轉為擴音,從辦公椅上站起來,重新綁好我居家褲的抽繩,將繩子拉得更緊了一些。這套柔軟的黑色運動服是XL尺寸的,穿在我身上寬大得十分怪異。不是我的衣服,是他的;德克斯再也穿不上了。無論過了多久,我都無法習慣這一點。
「嗯,可能吧,」我邁開步伐走向書架,再回到書桌邊,心想著自己是不是瘋了。
「拜託,梅瑟,拜託,梅瑟,陪審團成員已經選出來了,那些無聊的行政流程也都結束了,現在一切都攤在鏡頭前了,妳只需要去挖出那個瘋狂母親的細節就好。」我邊走邊聽凱薩琳用極快的語速和語帶哄騙的編輯口吻說著話,彷彿回到我們都還在《城市雜誌》工作的時光,那時她與我和其他下屬溝通也都是這種語氣。今年她開始為雅博出版集團擔任組稿編輯,雅博是一間超級大型企業,《城市雜誌》和許多刊物都是這間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出版品,還包含犯罪實錄的書系。
「我知道妳一定會想,『這不就是波士頓港的另一具屍體而已嗎?』」她繼續說,「但妳得明白這個案子不一樣!這可不是不良少年襲擊了同夥的抓耙子,也不是某個海洛因癮君子虐待自己的小孩,更不是什麼幫派械鬥。這次的凶手是一位年輕貌美的鄰家媽媽,就連她的名字『艾許琳』都這麼好聽。打開電視就會看到她的報導,還有她被捕時那副噘著嘴、蠻橫的模樣。我們希望妳能描寫出那種……妳知道的,表面上看似是典型美好的市郊家庭,私下卻充滿了痛苦與折磨。妳能賦予這些敘述真實感。」
真實感,知道了。我是個作家,是說故事的人,我將真實事件當作元素,並將這些元素變得引人入勝,但這個故事不需要過多的加油添醋。
「就像《冷血》那種非小說和報導文學。」凱薩琳接著說下去,彷彿我已經答應了一樣,「楚門.卡波提也只想像了其中一部分而已,就是編造角色之間的對話,他還能寫些什麼?但妳可以的,梅瑟,我知道妳可以。」
「嗯……好吧,」我說,「那就這樣吧。」我讓她以為自己說服了我。
「太棒了!我會再用電子郵件把文書資料寄給妳。沒有人比妳更適合這份工作了,妳一定會做得很完美。」凱薩琳說,「噢,抱歉,親愛的,妳知道我的意思。妳還好吧?」
「當然,」但她並不知道情況有多糟,「保持聯絡。」
我掛了電話,望向書房的窗戶,望向屋外我們的—我的石板路,還有我們—我身處的寧靜社區,眼前是九月早晨一片祥和的綠色景致,彷彿一切都一如既往;彷彿我的蘇菲仍在世,還有德克斯也在。接下這本書竟能帶給我這種感受。
「下地獄吧,艾許琳.布萊恩。」我說,「這是獻給你們的,親愛的。」
但當然,他們已經不在這裡了,無法向我說一聲謝謝。
2.
「妳是梅瑟.漢尼西嗎?」我打開前門,一個穿著藍色防風外套的男人查閱了手中的文件夾,「我們送來法庭的視訊設備,小姐,請問要放在哪裡?」
凱薩琳想必很有信心我最後會答應她。星期一早上七點十五分,我簽收了八個紙箱的視訊設
備,手裡拿著我的咖啡,在一大群穿著法蘭絨襯衫的男人忙著把所有東西拖進書房時,盡量不要擋到他們的路。他們從箱子裡拿出一臺銀色的螢幕、一個銀色的滑鼠、兩座鋁製的喇叭和兩臺黑色的路由器,接著解開橘色的傳輸線和白色的電源線,將線材全部安插好,如此就能像電視臺和廣播電臺一樣連線法庭的現場實況了。現在我的書房布滿了彩色的電線和延長線,看起來一片混亂,而我就這樣來到了波士頓寶寶的開庭現場。
「有沒有辦法錄下開庭過程,而不是只能同步觀看?」我問了其中一位工程師。
「可以啊,有辦法,」他說著,一邊用手機傳訊息,「但妳沒有設備。」
好吧,我會用我的iPad 側錄下來,很陽春的辦法,但把影片儲存在平板電腦裡,可以讓我回頭確認要引用的句子,或回顧整個訴訟過程。九十分鐘後就要開庭了。
這群人離開之後,我把他們散落一地的氣泡墊和保麗龍都集中在一起,拖到餐廳,再一路拖到地下室。他們叫我保留包材,等訴訟案結束後再來收回。
「他們為什麼不能自己拿?」我對著紙箱喃喃自語,一邊將東西拖下滿是灰塵的儲藏室樓梯,然後打開燈。「真不敢相信我要下來這裡。」
地下室是我過往人生的墓地,每當我不忍再看到某樣東西,但又捨不得扔掉的時候,就會把它藏起來,像是蘇菲的第一張嬰兒床,也是德克斯小時候用過的,是白色藤編的款式。德克斯的母親當年將這張小床送給我們,眼裡含著淚水。我們把蘇菲抱在懷裡,熱切地收下了它。等她一離開,德克斯便火速將這個搖搖欲墜的老舊小床拖進地下室,聲稱父親的職責就是要保護家庭。儲藏室裡還擺著祖母的婚禮瓷器,上面鑲著金邊,是我媽送的,她在遺囑中說要留給我們;德克斯母親送的許多茶具也擺在這裡。另外還有我們的婚禮相簿,某個阿姨曾告訴我,婚禮會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但她錯了。那天颳著十月的冷風,在南塔克特島,我們裹著毛毯瑟瑟發抖,一邊衝到斯康賽海灘,然後奮力扔掉手中的毯子,冷空氣讓我們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但我們拍下了一張美麗的照片。
月光下,我赤著腳,身穿白紗,在德克斯的懷裡開懷笑著。那並不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因為接下來的每一天都越來越好,直到蘇菲來了,那是另一個最美好的日子。
然後,一切就這麼停止了,再也沒有美好的時光。
我把箱子丟在樓梯最下面的一階,關上地下室的燈,也關上了我一部分的人生。我在黑暗中踏上階梯,穿過餐廳,來到廚房。
波士頓寶寶。
我不需要任何一本心理學入門書來解釋何謂移情,現在艾許琳.布萊恩已經不再是干擾我的情緒問題或潛在健康威脅,她是我的工作。
我往烤麵包機裡猛塞了幾片土司,煮了咖啡,然後在一旁等著,因為這臺烤麵包機有點難搞。
之後我把食物全都拿到書桌上,我要開工了,我將再一次成為原本的那個我。
回到書房,我坐在辦公椅上,輕晃滑鼠,並把喇叭的音量調大,但螢幕仍舊沒有畫面、沒有任何聲音、一片空白。
就像我的人生?不,我現在又有目標了。一個小女孩,屍首被海浪沖到城堡島海灘上。
波士頓寶寶。
還有一樁她媽媽被控謀殺的訴訟案。那個女人過去一年被關押在牢房裡,這是她應得的。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她還有很多歲月要待在裡面。她殺了自己的女兒,然後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她對每一個人撒謊,煞有介事地假裝泰莎在別的地方。警方指出,除了艾許琳.布萊恩之外,沒有任何人有動機、手法和機會去做。我很幸運,艾許琳.布萊恩的辯護律師是德克斯的老同事。幸運,對,德克斯死了,而我獲得一個人脈。
但另一種不帶諷刺的幸運,是這個審理中的案子越來越鋪天蓋地,報紙、廣播、電視、網路全都大肆報導,我敢打賭,對艾許琳.布萊恩的憎恨讓電梯裡的陌生人都能同仇敵愾,而那個怪物被判終身監禁肯定也會是這本悲劇小說的必然結局。
「有罪!」我說,比畫著一隻手指來強調,即使……是啊,即使沒有人在這裡聽我說話。
波士頓寶寶訴訟案──第一天。我在筆記型電腦上輸入標題。
真正的新聞標題已經不再稱受害者為「波士頓寶寶」了,取了這個名字的那位警察後來證實她的本名是泰莎.妮可.布萊恩。
兩個月後,他們逮捕了泰莎的媽媽。我重看了好幾次新聞上她被逮捕的三十秒畫面,凱薩琳說得對,剪輯實在十分老套。艾許琳.布萊恩被戴上了手銬,她哭喪著臉,身上的黑色緊身T恤又皺又凌亂,但看得出來她長得很漂亮。人們躲得遠遠地觀察她,對此議論紛紛。之後她便遭羈押,去為謀殺自己的孩子懺悔。我無數次就這麼獨自坐著,思索她當時究竟是什麼感覺。
艾許琳.布萊恩,整個麻薩諸塞州都深惡痛絕的女人,甚至可能是全國上下都痛恨的女人。
法官富蘭克林.威姆斯.格林十分有先見之明,預先考量到開庭時勢必會有大批一心想搶新聞的記者和攝影師蜂擁而至,於是便要求法院在法庭內架設四臺攝影機,其中還有一架「艾許琳專用機」,專門鎖定這名被告的臉。每一架機器的取景角度都設置得非常嚴謹,分別拍攝薩福克高等法院三〇六號法庭內的各個位置,但不會拍到陪審團的成員,也不會拍到旁聽的民眾。
這些人將會提出和我相同的問題。
她為什麼要這麼做?
21*14.8*2.1
25 開
Part 1
Part 2
Part 3
Epilo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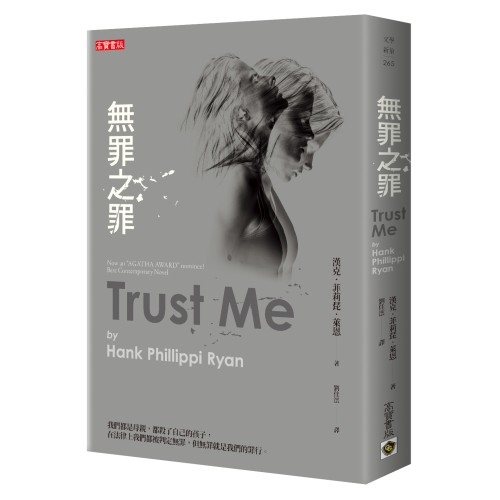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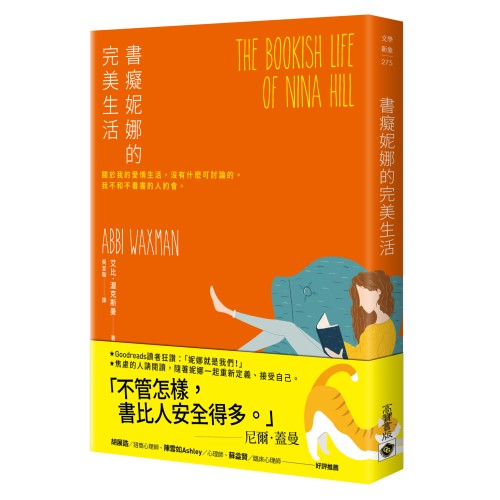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下)套書【不分售】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