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我的錢是用老辦法得來的,就是在某個有錢親戚將死之際對他倍加關懷。
───邁爾康.富比士(Malcolm Forbes)
富豪們的你爭我奪,結局是皆大歡喜,亦或多敗俱傷?
當尼可拉斯·楊(尼克)得知祖母尚素儀即將不久於人世,他終於結束冷戰回到泰瑟爾莊園,守在奶奶的床邊。但他並不孤單,因為所有楊氏、梁氏、尚氏家族全都在這時跑回莊園盡孝道,以博得奶奶歡心,期待能將無盡財產收入口袋。其中,泰瑟爾莊園(位於新加坡心臟地帶64英畝土地上的一座超級龐大莊園)是最主要的爭奪目標。
在這場遺產爭奪戰中,尼克對於童年時代的回憶變成了炒作和貪婪孳生的溫床,感到痛心疾首,誓言要將莊園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照著阿嬤的指引,一步一步揭開泰瑟爾莊園的神祕面紗。這是一座豪宅,更是一幢牽引歷史的古城,它的命運萬眾矚目……
跟著線索來到泰國,尼克在一個保險箱發現了阿嬤年輕時寫的日記,日記裡有一封英國國王的親筆信。
素儀的家族在過去打仗期間為英國政府工作,並提供泰瑟爾莊園作為庇護所,因此英國國王特頒勳章表揚。
擁有這項驚人意義的泰瑟爾莊園,絕不是能被當作拍賣物品兜售的古宅,尼克是否能順利聯手多人,籌到龐大資金,拯救岌岌可危的莊園?
擺脫前夫魔爪的艾絲翠,離幸福僅差一步之遙,卻迎來一道道精神重擊。加諸在她身心上的枷鎖,是否成了再次踏上紅毯的絆腳石?
富豪們的私人飛機,將帶我們從新加坡裝潢典雅的豪宅到蘇祿海僻靜的私人島嶼,到印度宮殿外見證一場意外的求婚,再到泰國皇室發覺驚人的祕密。
一連串複雜的人物關係與豪門背景攤開來,原來,富豪們錢很多,但問題更多。
遺產、愛情、自由……所有愛恨情仇、明爭暗鬥,是否終將雨過天晴?
人氣暢銷作家 螺螄拜恩
說書人 NeKo嗚喵
───瘋狂推薦
困擾一
去到海濱別墅所在的世外小島,卻發現自己在某間豪華餐廳的固定座位上坐了人。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巴哈馬哈勃島
貝蒂娜.奧蒂茲梅納不習慣等待。如今身為邁阿密汽車零件大亨赫曼.奧蒂茲梅納的妻子,在每間她選擇光顧的餐廳都備受尊敬,一進門就被領至想要的座位上。今天她想在「熙熙」(Sip Sip)位於露台角落的座位用餐,這是她在哈勃島最喜歡的午餐地點。她本想一邊吃著羽衣甘藍凱撒沙拉,一邊坐在舒適的橘色帆布摺疊椅上,欣賞碧綠色的海水輕柔地拍打海岸,不料有一群喧鬧的客人霸佔露台,似乎不急著離開。
貝蒂娜悶悶不樂地看著這群遊客在陽光下開心地享用午餐:看他們寒酸的樣子……女人曬那麼黑,臉上盡是皺紋,皮膚鬆弛下垂,也沒有適當的拉皮或打肉毒。她突然很想走過去每人發一張她皮膚科醫生的名片;男人嘛,就更糟糕了!一身皺巴巴的舊襯衫加短褲,戴著在鄧莫爾街的小飾品店買的便宜草帽。這樣的一群人到底為什麼會來這裡?
這塊三哩長的樂土包含一片純樸的粉色沙灘,是加勒比海鮮為人知的地方。這個富豪們的天堂有著冰沙色調、古色古香的小木屋、魅力十足的精品店、改建旅館的海濱別墅以及五星級餐廳,實可媲美聖巴瑟米(Saint Barthes)。在讓遊客登島前,應該先考考他們的時尚常識才對!感覺自己已經忍無可忍,貝蒂娜一陣風似的衝進廚房,直奔站在主爐前、一頭金色精靈短髮的女人,身上那件Pucci鉤織土耳其長衫上的流蘇大幅度地擺動。
「茱莉,這是怎麼回事?我等了十五分鐘還沒有人帶位!」貝蒂娜對著餐廳老闆發牢騷。
「抱歉,貝蒂娜,今天妳運氣不好,露台上那組十二位的客人比妳早來。」茱莉答道,把一碗香辣海螺肉遞給等在一旁的服務生。
「但露台是你們最好的位置!到底為什麼要讓那群遊客把座位全佔了?」
「因為那個戴紅色漁夫帽的遊客是格倫科拉公爵,他們剛從溫德米爾島搭船過來—停在岸邊的那艘船就是他的皇家休斯曼,那應該是妳見過最美的帆船吧?」
「我對大船沒興趣。」貝蒂娜氣憤地說,暗地裡卻對頭銜響亮的人十分憧憬。她透過廚房窗口,用不同的眼光審視露台上的那群人。這些英國貴族真是群怪胎。的確,他們平時穿戴的是在薩佛街訂製的服裝和祖傳皇冠,但只要一旅行,就會變得非常邋遢。
貝蒂娜這時才注意到鄰桌坐了三個古銅膚色、體格健壯的男人,穿著合身的白T恤和黑色防摔褲。他們沒有點餐,只是警惕地坐在座位上,慢慢喝著氣泡水。「我猜那些人是公爵的隨扈?簡直明顯到不行。難道他們不知道會來布里蘭的都是億萬富翁,帶保鑣不是我們的作風嗎?」貝蒂娜嘖嘖喟嘆。
「事實上,那是公爵招待的貴客帶的保鑣,這些客人進來前,他們把整個餐廳掃過一遍,連冷凍室也不放過。看到那桌最裡面的那個華人了嗎?」
貝蒂娜瞇起藏在Dior Extase太陽眼鏡後的眼睛,看向那個七十多歲、發福禿頭的亞洲人,白色短袖高爾夫球衫加灰色長褲,一身不起眼的打扮。「噢,我剛才根本沒注意他,他很有名嗎?」
「他是阿爾弗雷德.尚。」茱莉壓低聲音。
貝蒂娜忍不住笑出聲來。「他看起來像他們的司機,不覺得他跟〈鷹冠莊園〉(Falcon Crest)裡載著珍.惠曼到處跑的那個人很像嗎?」
茱莉試圖專心將一塊鮪魚表面烤至近乎完美,抿嘴微笑,搖搖頭說:「我聽說那個司機是全亞洲最有權勢的人。」
「妳說他叫什麼名字?」
「阿爾弗雷德.尚。人家告訴我,他是新加坡人,常年住在英國。他的莊園有半個蘇格蘭那麼大。」
「我從未在任何富豪排行榜上見過他的名字。」貝蒂娜嗤之以鼻。
「貝蒂娜,我相信妳很清楚,這世上就是有人有錢有勢到不會出現在那些排行榜上!」
困擾二
每年預付一百萬聘請的私人醫生本應隨時待命,卻忙著照顧其他病患。
坐在露台上眺望哈勃島傳說中的海灘,阿爾弗雷德.尚驚嘆於眼前壯觀的美景。是真的—沙灘真的是粉紅色的!
「阿爾弗雷德,你的龍蝦起司餡餅要涼了!」格倫科拉公爵突然出聲,打破他的遐想。
「你大老遠把我拉來這裡就是為了這個?」阿爾弗雷德說,盯著面前那盤擺盤巧妙的三角形厚餅。撇除他住在墨西哥城的廚師朋友史利姆做的菜,他其實對墨西哥料理不感興趣。
「先吃吃看再說。」
阿爾弗雷德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默默地感受半脆玉米餅、龍蝦和酪梨醬搭在一起所產生的魔力。
「很棒吧?這幾年我一直在說服威爾頓的大廚複製這道菜。」公爵說。
「他們家的菜半個世紀來不曾變過,要把這道菜加到菜單裡感覺不太可能。」阿爾弗雷德笑了笑,撿起掉在桌上的龍蝦肉丟進嘴裡。就在這時,他放在褲子口袋的手機震了起來。他拿出手機,煩躁地盯著螢幕。大家都知道他和公爵一年一度的釣魚之旅是不容打擾的。
螢幕顯示的來電者是:泰瑟爾二樓警戒。
是他姊姊素儀打來的,唯有她的電話無論何時他都會接。他立刻按下通話鍵,一個意料外的聲音從另一頭傳來,用廣東話說:「尚先生,我是阿玲。」
他頓了幾秒才想起這個跟他說話的人是泰瑟爾莊園的管家。「噢……玲姐!」
「我家太太要我打電話給您。她今晚人不太舒服被送到醫院,我們認為是心臟病。」
「妳說你們認為是什麼意思?是心臟病還是不是?」阿爾弗雷德語氣慌張,一下從裝模作樣的英國腔換成廣東話。
「她……她沒有胸痛,但她流了很多汗,還吐了。她說她感覺自己心跳很快。」阿玲緊張地結巴起來。
「溫教授去看了沒有?」阿爾弗雷德問。
「我打教授手機,直接進到語音信箱,又打去他家,對方說他人在澳洲。」
「為什麼是妳一個人在連絡?維多莉亞不在家嗎?」
「尚先生,維多莉亞不是去英國了嗎?」
阿啦嘛,他完全忘了他的外甥女—素儀的女兒,現居泰瑟爾莊園—此時此刻正在他薩里的家裡,不用說,絕對是跟他的妻女一起展開一場八卦饗宴。
「費莉希蒂呢?她去醫院了嗎?」阿爾弗雷德問起素儀住在附近的大女兒,她家就在那森路上。
「今晚無法聯絡梁太太。她家女傭說她去了教堂,她在教堂時通常會關機。」
這一個一個,真是沒用!「叫救護車了嗎?」
「沒有,她不想坐救護車。是維克拉姆開車,在她的侍女和兩名廓爾喀兵的陪同下去了醫院。但她臨走前跟我說您知道如何與溫教授取得聯繫。」
「好了好了,我會處理。」阿爾弗雷德惱怒地說,掛上電話。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殷切地看著他。
「我的天,聽上去挺嚴重的。」公爵開口,擔憂地抿緊嘴唇。
「容我失陪一下……各位請繼續。」阿爾弗雷德從座位上站起來。他的隨扈跟著他穿過餐廳,走出門外進到花園。
阿爾弗雷德利用快速撥號打了另一通電話:溫教授家。
一個女人接起了電話。
「是奧莉薇亞嗎?我是阿爾弗雷德.尚……」
「噢,阿爾弗雷德,你找法蘭西斯嗎?」
「對,我聽說他現在人在澳洲?」到底為什麼他們要每年付給這個總是鬧失蹤的醫生一百萬?
「他一個小時前剛出發前往雪梨,明天要幫那個奧斯卡得主做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所以他現在在飛機上?」阿爾弗雷德打斷她的話。
「對,你找他的話,他會在幾小時內抵達……」
「把他的班機號碼給我。」阿爾弗雷德嚴斥道,隨即轉向他的隨扈人員。「誰有新加坡的手機?馬上幫我接通總統府。」
接著對另一個隨扈說:「再幫我點一份龍蝦起司餡餅。」
困擾三
班機被迫降落的時間,還不夠喝完一杯香檳王(Dom Perignon)。
同一天在印尼東爪哇省(East Java)……
當這架巨型雙層客機空中巴士A380-800攀升到舒適的飛行高度三萬八千呎時,頭等艙的乘客不再需要紀梵希絲綢被,大多數都舒服地窩在座位上,瀏覽新上映的影片。片刻後,新加坡航空飛往雪梨231號班機機長在飛越印尼領空時,收到來自雅加達飛航管制塔台非比尋常的指示。
飛航管制員:新加坡231號,這裡是雅加達。
機長:這裡是新加坡231號,請說。
飛航管制員:我接到指示要你們立刻掉頭,返回新加坡樟宜機場。
機長:雅加達塔台,你們要我們返回樟宜機場?
飛航管制員:是的,請你們立刻將飛機折返。我這裡有修正過的飛行航線可供複製。
機長:雅加達塔台,為什麼需要修正飛行航線?
飛航管制員:我沒有得到相關訊息,但這是由民航局直接下達的命令。
兩位駕駛難以置信地面面相覷。「真的要這麼做嗎?」機長直接說出內心的疑惑。「這樣我們在降落前,就必須傾倒二十五萬升的燃料!」
這時候,機上的選擇呼叫無線電系統亮燈,一個訊息傳了進來。副機長很快地讀了後,一臉不可思議地看向機長。「我靠!是天殺的國防部長傳來的,他說馬上返回新加坡!」
當飛機在起飛後三個鐘頭出於意外返回樟宜機場時,機上乘客全被這個異常事件搞得一頭霧水,人心惶惶。而後對講機傳來廣播通知:「各位貴賓您好,由於意外事故,我們已緊急返回新加坡。請您留在座位上並繫好安全帶,本航班將在加油完畢後立刻起飛前往雪梨。」
兩名穿著深色西裝的男子一身隆重地登上飛機,走近坐在編號3A座位的男人—法蘭西斯.溫教授,新加坡的首席心臟病專家。「你是溫教授?我是SID的萊恩.陳中尉,請跟我們來。」
「我們要下飛機?」溫教授問,全然不知所措。上一秒他還在看《控制》(Gone Girl),下一秒飛機便回到了新加坡,他甚至尚未從這部電影令人心痛的劇情恢復過來。
陳中尉簡短地點頭。「是的,請務必攜帶所有行李—你不會再回到這架班機上。」
「但、但……我做了什麼?」溫教授突然感到一陣不安。
「別擔心,你什麼也沒做,但我們得把你帶下飛機。」
「只有我要下飛機?」
「是的。我們會直接送你到伊麗莎白醫院,有人要求你前去照顧一位VVIP病患。」
溫教授這才明白尚素儀肯定出事了,因為只有尚家擁有這種權力—讓載著四百四十位乘客的飛機返航。
第一部
瑞士,達佛斯
艾迪森.鄭抬頭盯著這個白色大禮堂挑高的蜂窩狀天井,感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來了,我終於來到這裡了!這麼多年來,他以奧林匹克等級的努力打通關係網,現在終於實現願望—受邀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在達佛斯舉辦的年會。只有受邀者有資格參加,這個赫赫有名的活動是屬於全球上流人士的聚會。
每年一月,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元首、政治家、慈善家、企業執行長、科技領袖、思想領袖、社會運動家、公益創業家,當然還有影星都會搭乘私人飛機來到這個瑞士阿爾卑斯山的滑雪勝地,入住豪華飯店,穿上價值五千美元的滑雪外套和滑雪靴,展開關於全球暖化和不平等現象加劇等緊迫議題間有意義的對話。
而現在艾迪也成了這個超級俱樂部的一員。作為列支敦堡集團新任命的全球私人銀行執行副主席,他人就站在會議中心裝潢前衛的禮堂,呼吸稀薄的空氣,並在禮堂椅鉻合金的椅腳上捕捉自己的倒影。他穿著一件訂製的Sartoria Ripense西裝,裡面另外加了十層羊毛內襯,這樣他就不必穿上滑雪外套保暖;最近新買的Corthay松鼠絨面革恰克靴有特殊的防雪橡膠鞋底,可讓他免於在濕滑的阿爾卑斯街道滑倒;手腕上戴著新到手的錶款—限量版的朗格陀飛輪腕錶,剛好從他的袖口露出來,剛好可讓其他愛錶族看見。但最重要的是掛在這身光彩奪目衣裝外的東西—帶有黑色掛繩的塑膠徽章,中間印有他的大名艾迪森.鄭。
艾迪摩挲著表面光滑的塑膠徽章,彷彿這是達佛斯之神親自授予他的珠寶護身符。這個徽章將他和會議中其他不重要人士區隔開來。他並非什麼公關、記者,或某個定期參加的與會者。這枚下方畫有藍線的白色徽章意味著他正式代表的身分。
艾迪環顧周遭小聲交談的人們,想找看看有哪個專權者或企業家是他認識、可與之接觸的。他眼角餘光瞄見一個身材高挑、穿著橘色滑雪風衣的華人男子,正從禮堂側門往內窺看,似乎是迷了路。等等,我認識他,那不是查理.胡嗎?
「喂—查理!」艾迪匆匆走向查理,大聲喊道。等著看我的正式代表徽章吧!
查理認出他後露出笑容。「艾迪.鄭!你從香港飛來的?」
「其實我是從米蘭來的,我才剛參加艾綽(Etro)男裝秋季時裝秀—坐在第一排。」
「哇,身為《香港快速時尚》最佳著裝男士之一的工作還滿嚴肅的嘛?」查理打趣地說。
「其實我去年入選了最佳著裝名人堂。」艾迪認真地回答。他很快掃了查理一眼,注意到他穿著卡其色工裝褲,橘色滑雪風衣下則是深藍色的高領毛衣。真可憐—他年輕時打扮那麼出眾,現在卻穿得跟其他普通科技宅沒什麼兩樣。「查理,你的徽章呢?」艾迪問,自豪地把自己的秀給查理看。
「噢,對,我們要一直戴著吧?謝謝你提醒我—我把它丟在我的郵差包裡了。」查理翻了幾秒鐘的包包,才把徽章拿出來。艾迪瞥了一眼,好奇心瞬間轉為驚愕。查理拿著一個白色徽章,上面貼著一張閃爍的鐳射貼紙。
幹他媽的,這是大家夢寐以求的徽章!只有各國首腦拿得到!他目前也只見比爾.柯林頓戴過!查理是怎麼拿到的?他不過是開了家全亞洲最大的科技公司而已啊!
為了掩蓋他的忌妒,艾迪脫口而出:「嘿,你要來聽我的專題—『天啟亞洲:若中國泡沫經濟真的破裂該如何挽救資產』嗎?」
「其實我正準備出席IGWEL 7演講,你的專題什麼時候開始?」
「下午兩點,你要講什麼?」艾迪問,心想他或許可以跟查理一起參加。
「說實話,我什麼也沒準備。我猜安格拉.梅克爾和那些北歐人只想跟我討教問題。」
就在此時,查理的助理愛麗絲走了過來。
「愛麗絲,看我遇到誰了!我就知道我們遲早會遇到同樣香港來的人!」查理說。
「鄭先生,很高興在這裡見到你。查理—可以跟你說句話嗎?」
「當然。」
愛麗絲瞥了眼艾迪,發現對方還站在原地,看上去一副殷切期盼的模樣,讓她難以開口。「呃……你能跟我來一下嗎?」她委婉地說,帶著查理走進旁邊的接待室,裡面擺了好幾張躺椅和方形咖啡桌。
「什麼事?妳還沒從和菲瑞同桌吃早餐的震撼恢復過來嗎?」查理調侃道。
愛麗絲緊張地笑了笑。「有個狀況持續了整個上午,我們在詳細了解以前一直不想打擾你……」
「妳直說吧……」
愛麗絲深吸口氣後開口:「我剛接到香港保全主管的訊息,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克蘿伊和達芬妮失蹤了。」
「妳說失蹤是什麼意思?」查理很震驚,因為他派人全天候跟著他的女兒,無論接送都是由他手下受過英國特勤隊培訓的保全部隊負責。失蹤不會是他們人生中的問題。
「重慶小組計畫下午三點在拔萃女小學外頭接她們,卻找不到定位。」
「找不到定位……」查理愣愣地喃道。
愛麗絲接著說:「傳簡訊克蘿伊沒有回,達芬妮也沒有去下午兩點的合唱團。他們以為她大概又跟上次一樣,和她的同班同學凱瑟琳.陳溜去優格冰淇淋店,後來發現凱瑟琳去了合唱團,達芬妮卻沒出現。」
「她們兩個有啟動警戒碼嗎?」查理問,試圖保持冷靜。
「沒有,她們的手機一直都是停用狀態,所以我們無法追蹤她們。二○四六小組已跟郭中校聯絡—香港警方目前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我們也動員四個小組進行搜索,校方現在正與田先生一起檢查校內所有監視錄影機。」
「你們應該有人問過她們媽媽了吧?」查理分居的妻子—目前住在他們位於太平山的房子—孩子們每隔一週會到她那邊住。
「找不到伊莎貝爾,她告訴管家她中午要在九龍木球會跟她母親吃飯,但她母親說她們已有一個星期沒聯絡了。」
這時候,愛麗絲的手機響了起來,她很快接起來,默默聽著,時不時點頭。查理若有所思地看著她。不會的,不會發生這種事。十年前他弟弟羅勃遭三合會綁架,這一切彷彿似曾相識。
「好,多謝多謝。」愛麗絲說著,掛斷電話。她看向查理,開始彙報:「天使小組的負責人打來說,伊莎貝爾可能出國了。他們詢問過二樓的女傭,發現她護照不見,但出於某個原因她沒帶行李箱。」
「她不是在做某個新療程嗎?」
「是的,但顯然她在這週跟精神科醫生約好的時間沒有出現。」
查理重重地嘆了口氣,這不是好現象啊。
14.8*21*2.6
25 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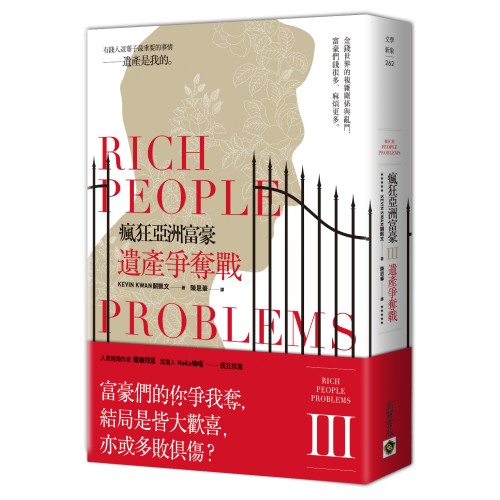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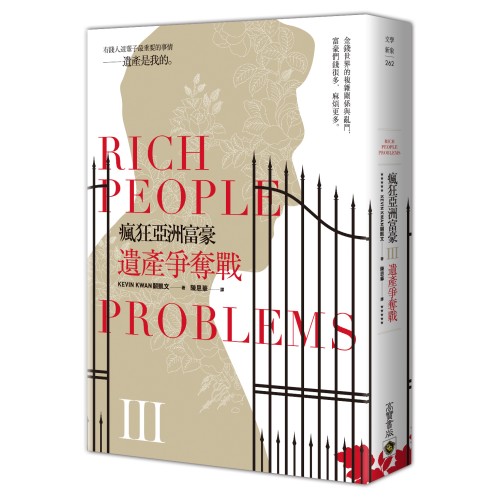











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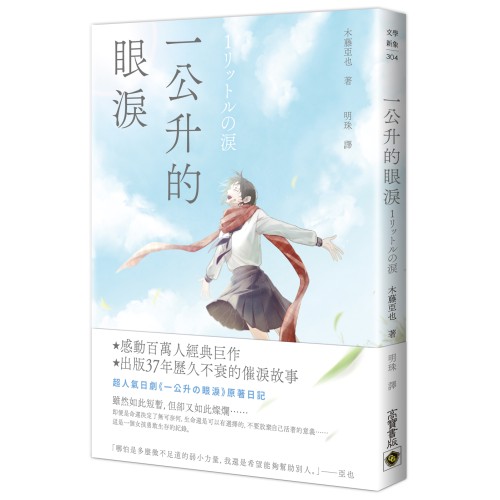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