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限定
瘋狂亞洲富豪(電影書衣典藏版)
NT$315
NT$399
-
作者關凱文 Kevin Kwan
-
譯者陳思華
-
ISBN9789863615569
-
上市時間2018-07-25
- 電子書
- 本書無電子書 /
-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你無法想像這些富豪們多有錢,因為他們比上帝還有錢!
一起開始一場爆笑浮誇、極度拜金的荒唐之旅。
★華納兄弟改編電影,2018年8月24日嫁入豪門!
★《出神入化2》導演朱浩偉執導
★《菜鳥新移民》吳恬敏、混血帥哥亨利・高丁、楊紫瓊、《醉後大丈夫》鄭肯聯手主演
★富豪系列首部曲,甫上市即登上暢銷書榜,全球狂賣100萬冊
「唯一讓這些紅毛高賽尊重我們的方法,就是把大把的錢砸在他們臉上,直到他們下跪求饒為止。」───查理・胡(新加坡超級暴發戶科技大亨胡浩連的長子,本來有機會舉行亞洲史上最奢華的婚禮,可惜三十九克拉的鑽戒被拒絕了。)
一群荒誕離奇、陰險腹黑的超級富豪,
諷刺又寫實地呈現有錢人家的優越感與家庭矛盾,帶人一窺所謂上流社會最不為人知的瘋狂生活。
當瑞秋・朱答應與男友尼克・楊一同前往新加坡參加友人婚禮、拜訪尼克的家人,她想像的是一個小門小戶的家庭,並期待跟這個將來可能步入禮堂的男人共度兩人時光。
沒想到迎接瑞秋的卻是令人瞠目結舌的超級大豪宅,以及一群她所見過最瘋狂古怪的人,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的男友是亞洲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黃金單身漢,有多少女人都盼望著晉升為楊太太,這時的瑞秋理所當然地成為眾矢之的。
在新加坡,尼克帶著瑞秋走遍所有他喜歡的地方,置身於這個富豪圈子之中,比起車子,他們更常搭飛機;比起知名觀光景點,他們更喜歡私人度假村。
看似享盡榮華富貴的瑞秋卻體驗到了此生經歷過最不堪的羞辱,在有錢人家勢利的眼中,她是一個為錢而跟尼克交往的女人;她是奢望麻雀變鳳凰的心機女……
這樣與她格格不入的家庭,瑞秋認真思考與尼克繼續發展下去的可能性,究竟他們能不能打破亞洲傳統「門當戶對」的觀念,攜手走向未來呢?
人氣暢銷作家 螺螄拜恩
電影評論家 雀雀
------瘋狂推薦(順序按筆畫排列)
瑞秋
聖莎拉島
所有的單身女伴都坐在長桌邊,頭頂遮著橘色絲綢布搭起的波浪形棚子,腳下踩著天然的白沙,四周環繞著明亮的銀燈,邊欣賞夕陽邊享受晚宴。暮色下的柔波變成藍綠色的泡沫,可以成為刊登在康泰納仕集團旗下的《旅遊者雜誌》的照片,只是晚宴席間的話題讓人有點掃興。當第一道奶油生菜搭配棕櫚心佐椰奶醬上桌時,坐在瑞秋左手邊的一群女生開始談論另一個女生的男朋友。
「所以妳說他才剛升為資深副總經理,但他是從事零售方面的工作,而不是投資銀行業,對不對?我問過我男友羅德里克,他覺得幸運的話,賽門的底薪大概會落在六十到八十萬間。而且沒有像投資銀行業有上百萬的獎金。」蘿倫.李嗤之以鼻地說。
「另一個問題是他家,賽門不是老大,他是五個小孩中第二小的。」帕可兒果斷地說:「我
爸媽跟陳家很熟,讓我告訴妳,雖然他們家的作風令人尊敬,但他們不是妳我會認為有錢的人家,我媽說他們家總資產最多也就兩百萬吧。把它分成五份,運氣好賽門最後會拿到四十萬的遺產。而那會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他爸媽都還很年輕,他爸不是還要出來選議員嗎?」
「我們只是希望妳有好的歸宿,伊莎貝爾。」蘿倫說,同情地拍拍她的手。
「但───但我覺得我真的愛他───」伊莎貝爾吞吞吐吐地說。
芙蘭雀絲卡.邵插嘴道:「伊莎貝爾,我就直說了,因為其他人都太客氣,是在浪費妳時
間。妳付不起愛上賽門的代價。我來幫妳分析,我們把條件放寬一點,假設賽門一年可以賺少得可憐的八百萬,扣除稅收和中央公積金(CPF)後,他的實得工資只剩下五十萬。只有那一點錢妳要住哪兒?想想看,一個房間就要一百萬,而妳至少要有三間房,所以妳會花三百萬住在武吉知馬的公寓。一年就要貸款十五萬加上財產稅;假設你們生了兩個小孩,妳想讓他們去上好學校。一個人一年學費是三萬元,加起來就是六萬元,然後兩個小孩上家教一年各兩萬元,所以你們一年花在教育上的費用就要十萬;傭人和保母─兩個印尼或斯里蘭卡女傭還要再花三萬,除非妳要將其中一個換成來自瑞典或法國的互惠生,那幫傭費就是一年八萬元。那妳自己的花費又會是多少?妳至少每一季需要十件新衣服,這樣出入公共場合才不會沒面子。幸虧新加坡只有兩個季節───熱和更熱───所以保守估計,妳每一件衣服只需花四千元,所以一年下來妳的治裝費就是八萬。我再加上兩萬元讓妳每季買一個好的提包和幾雙新鞋。然後是妳基本的保養─頭髮、臉、手腳、蜜蠟除毛、眉蠟修毛、身體按摩、脊椎按摩、針灸、普拉提瑜伽、核心融合瑜伽和請私人健身教練,這些零零總總加起來一年又要花上四萬元。賽門的薪水到目前為止已經花了四十七萬,只剩下三萬元可拿來作其他用途。這麼一點錢妳要吃什麼,要給妳小孩穿什麼?妳又要怎麼一年去兩次安縵度假村放鬆呢?而我們還沒算妳在邱吉爾俱樂部和新加坡島鄉村俱樂部的會員資格呢!妳還不明白嗎?妳要跟賽門結婚根本是天方夜譚。如果妳有錢我們不會擔心,但妳的情況妳自己清楚。妳的青春年華正在流失,最好趁早節省損失,在事態太遲前,讓蘿倫介紹適合的北京富豪給妳認識。」
伊莎貝爾傷心得落淚。
瑞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跟這群人比起來,上東區的女孩簡直就是門諾會的成員。她試著把注意力拉回眼前的食物上。第二道菜才剛上桌─是一道出乎意料美味的挪威海螯蝦四季柑果凍陶罐派。可惜坐在她右側的女生正大聲地談論一對名字是阿歷斯泰和凱蒂的情侶。
「哎呀,我不明白他看上她哪裡。」克蘿伊.何哀嘆道:「她那假冒的口音、假胸部,什麼
都是假的。」
「我知道他其實看上她什麼。他看上的就是那對假胸,他也只需要看那個!」帕可兒笑著說。
「瑟蕾娜.胡跟我說她上禮拜在龍景軒碰到他們,凱蒂從頭到腳都穿Gucci : Gucci 的包包、Gucci 的繞頸綁帶背心、Gucci 的錦緞迷你褲和Gucci 的蟒蛇皮靴。」克蘿伊說:「她晚餐席間全程都戴著Gucci 的太陽眼鏡,就連在餐桌跟男友親熱也沒拿下來。」
「阿啦嘛!這也太俗了吧!」溫蒂低語道,摸了摸頭上鑲著鑽石及藍鑽的皇冠。
帕可兒突然越過桌子問瑞秋:「等一下,妳見過他們了嗎?」
「誰?」瑞秋問。因為她很努力地不去注意那群女生的談話,而不是聽她們說其他女人的壞話。
「阿歷斯泰和凱蒂!」
「抱歉,我沒有很注意聽───他們是誰?」
芙蘭雀絲卡瞄了瑞秋一眼說:「帕可兒,別浪費時間─很明顯瑞秋根本什麼人也不認識。」
瑞秋不明白為什麼芙蘭雀絲卡對她的態度這麼冷淡,決定不管她的批評,喝了一口灰皮諾葡萄酒。
「瑞秋,跟我們說說妳是怎麼認識尼可拉斯.楊的?」
「呃,其實沒什麼,我們都在紐約大學教書,是我的一個同事介紹我們認識的。」瑞秋回答,注意到全桌的視線都在她身上。
「噢,妳同事是誰呀?新加坡人嗎?」蘿倫問。
「不是,她是華裔美國人,她叫席爾薇亞.王───施瓦茨。」
「她是怎麼認識尼可拉斯的?」帕可兒問。
「呃,他們是在某個委員會認識的。」
「所以她跟他不是很熟囉?」帕可兒追問道。
「對,應該不太熟。」瑞秋回答,不禁有些納悶這群女生到底想知道什麼。「妳為什麼對席爾薇亞這麼有興趣?」
「噢,因為我也很喜歡幫朋友作媒,我只是很好奇為什麼妳朋友要介紹你們認識啦。」帕可兒微笑地說。
「這個嘛,席爾薇亞人很好,一直都想介紹對象給我,她只是覺得尼克很帥,而且會是完美的結婚對象───」話甫出口,瑞秋頓時覺得自己說錯話了。
「聽起來她對那個有做過功課嘛,不是嗎?」芙蘭雀絲卡發出尖銳的笑聲。
晚餐過後,其他女生都離開去到搭在碼頭、看起來搖搖欲墜的迪斯可舞廳,瑞秋獨自一人
前往海灘酒吧。那是一個富有畫意的涼亭,可眺望前方僻靜的小海灣。除了身材高大魁梧的調酒師,涼亭內空無一人。他在她走進酒吧時,咧嘴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小姐,需要來點什麼嗎?」他用幾乎滑稽誘人的口音問。見鬼了,亞拉敏塔的媽媽是只雇用風流倜儻的義大利人嗎?
「其實我只想喝啤酒,這裡有啤酒嗎?」
「當然。我看看,這裡有可樂娜、杜威、莫雷帝、紅線條,還有我個人最喜歡的獅子司陶特啤酒。」
「我沒聽過。」
「這是斯里蘭卡的啤酒,喝起來有奶油般的口感,帶點苦甜味,還有棕褐色的頭。」
瑞秋忍俊不禁,聽上去他彷彿在形容他自己。「若你真那麼喜歡,我就喝喝看吧。」
在他把啤酒倒進一個毛玻璃的高杯裡時,一個瑞秋之前從未注意到的女生晃進酒吧,在她身旁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感謝老天這裡還有別人會喝啤酒!我受夠那些難喝的低熱量雞尾酒了。」她說。她看上去是華人,卻說了一口澳洲英語。
「那乾杯吧。」瑞秋回答,把杯子朝她的方向動了動。她點了可樂娜,調酒師還來不及把酒倒進杯裡,她便一把抓過啤酒瓶。當她抬頭把啤酒一咕嚕的喝下肚時,他露出受傷的神情。「妳是瑞秋,對吧?」
「我就是。但如果妳找的是台灣那個瑞秋.朱的話,妳找錯人了。」瑞秋先發制人地開口。
她露出詫異的笑容,有些不明白瑞秋的意思。「我是艾絲翠的表妹蘇菲,她要我照顧妳。」
「噢,嗨。」瑞秋說。蘇菲友善的笑容和深邃的酒窩讓她卸下心防。不像其他女生互相競爭追尋度假的時尚感,她簡單穿著一件無袖棉襯衫及卡其短褲。她剪了頭乾淨俐落的短鮑伯頭,沒有化妝也沒戴任何首飾,只有手腕上戴了一支塑膠的Swatch 錶。
「妳有跟我們一起搭飛機嗎?」瑞秋努力喚起腦中的印象。
「沒有,我是自己飛過來的,幾個小時前才到。」
「妳也有自己的飛機?」
「不,我沒有。」蘇菲笑了起來。「還好加魯達印尼航空的經濟艙還有位置。我醫院有些工作要做,所以到今天下午才有空來。」
「妳是護士?」
「小兒科醫生。」
再一次,瑞秋又想起人不可貌相這句話,特別是在亞洲。「所以妳是艾絲翠跟尼克的表妹?」
「不,只是艾絲翠的表妹而已,梁家那邊的。她爸爸跟我媽媽是兄妹。但當然我也認識尼克───我們都一起長大。妳在美國長大,對不對?妳住哪兒?」
「我十幾歲的時候住加州,但我住過十二個不同的州。我小時候常常搬家。」
「為什麼常搬家?」
「我媽以前在中國餐廳工作。」
「她是做什麼的?」
「她通常是從服務生做起,但她總是能很快地升遷。」
「所以她就帶著妳到處跑?」蘇菲一副感興趣的樣子。
「對─那時候我們過著吉普賽人的生活,一直到我步入青春期後,才在加州定居。」
「妳會覺得寂寞嗎?」
「這個嘛,因為我只知道這種生活,所以對我來說還滿正常的。也因為如此,我對郊區商店街餐廳的裡屋很熟,我完全是個書呆子。」
「那妳爸爸呢?」
「我出生後他就過世了。」
「噢,抱歉。」蘇菲很快地接下去,後悔問這個問題。
「沒關係─我從沒見過他。」瑞秋露出微笑,試圖讓她放寬心。「而且其實也沒那麼糟。
我媽去上夜校,取得大學文憑,現在也成為成功的房地產經紀人好多年了。」
「真厲害。」蘇菲說。
「也沒有啦,我家其實就是那種老掉牙『亞裔移民成功的故事』,許多政治人物每四年會在選舉時拿出來誇耀的故事。」
蘇菲咯咯地笑了起來。「我知道尼克為什麼喜歡妳了───你們兩個都有著自嘲的幽默感。」
瑞秋笑了笑,轉頭看向碼頭的迪斯可舞廳。
「我耽誤妳去舞會的時間了嗎?聽說亞拉敏塔從伊維薩島請來很知名的DJ。」蘇菲說。
「跟妳聊天很開心,說真的,這是我一整天真正像樣的談話。」
蘇菲瞄向那群女生─大部分的人都隨著迪斯可裡震耳欲聾的歐洲舞曲貼著義大利侍者擺腰扭臀─聳了聳肩。「跟那群人在一起,我一點都不意外。」
「妳跟她們是朋友嗎?」
「有一些是,但大部分我都不認識,當然我認得出誰是誰。」
「她們是誰啊?有些人很有名嗎?」
「大概在她們自己的腦中有名吧。她們就是那種喜愛社交的女生,總是出現在雜誌上,參加所有慈善晚會。對我來說太招搖了。不好意思喔,但我在醫院輪十二小時的班,沒時間參加飯店舉辦的捐助會,我得先捐助我爸媽才行。」
瑞秋笑了出來。
「說到這個─」蘇菲補了一句:「我今天早上五點就起床了,所以我要去休息了。」
「我也跟妳一起去休息好了。」瑞秋說。
她們離開碼頭往木屋走去。
「我就住在這條走廊最後面那間別墅,有什麼需要就來找我吧。」蘇菲說。
「晚安。」瑞秋說:「跟妳聊天很開心。」
「我也是。」蘇菲說,再次露出深邃酒渦的笑容。
瑞秋回到她的別墅,累了一整天後,很高興終於能有一點祥和與寧靜的時刻。屋裡沒有開燈,但外頭皎潔的月光透過敞開的紗門灑了進來,牆面上映著蛇紋石的波紋。海面很平靜,海水靜靜地打在木屋地板的聲音,讓人有些昏昏欲睡。這個地方是夜泳的好去處,雖然她從沒做過這種事。瑞秋走向她的臥房找比基尼。當她走過梳妝台時,她注意到她掛在椅背上的皮背包似乎沾到了什麼液體。她走了過去,發現整個背包完全濕透,汙黃的水從包包的一角滴到地板上,形成一小片水窪。發生什麼事了?她打開桌上的檯燈,翻開前面的皮包蓋。她放聲尖叫,驚嚇地往後退,把檯燈撞到地上。
她的皮包裡裝了一條大魚,整個身體支離破碎,鮮血從魚鰓流了出來。在椅子前方的梳妝鏡上用魚血驚悚地寫著一句話:「嚐嚐這招,妳這拜金婊子!」
瑞秋和裴琳
坐上車的兩人很快地沿著植物園後方滿是落葉的路上蜿蜒向前,沿途尋找泰瑟爾大道。司機說他之前開過那條路,但現在似乎找不到。「GPS 上沒有顯示那條路真怪。」裴琳說:「這區域的路很複雜,這裡是少數幾個有這種窄巷的社區。」
這個社區讓瑞秋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這是她第一次看見在一望無際的草坪上建了這麼
多古老的大房子。「這地方大部分的路名聽起來還滿英國風的,納比雅路、古魯尼路、加勒普
路───」瑞秋說。
「以前英國殖民時期的官員都住在這裡─這個地方其實不完全是住宅區。這裡大部分房子都是政府的,很多都是大使館,像那棟門前有柱子的灰色巨大建築─那是俄羅斯大使館。尼克的奶奶一定是住在政府的公寓大樓─所以我才沒聽過。」
車速突然慢了下來,在一條叉路向左轉,開進另一條更窄的巷子。「這裡就是泰瑟爾大道,
所以穿過這條路應該就到了。」裴琳說。路旁大樹像蛇一般的粗壯枝幹伸了出來,遮在鋪了一層層茂密的蕨類植物的路面上方。這種植物長於原始森林,曾經遍布整個新加坡。忽然間,路開始向右彎,兩根白色的六角柱隨即映入眼簾,其間是一道淺灰色的低矮鐵柵門。路邊一個幾乎被繁茂枝葉遮掩住的生鏽門牌上寫著「泰瑟爾公園」。
「我這輩子從未走過這條路,這裡有公寓真奇怪。」裴琳只說得出這樣一句話。「現在怎麼辦?妳要打給尼克嗎?」
瑞秋正要開口時,一個印度警衛出現在門口。他身穿燙得筆挺的橄欖綠制服、頭上纏著笨重的頭巾,臉上的鬍子讓他看起來一副很嚴肅的表情。裴琳的司機慢慢地把車往前開,在男人走上前時開了窗戶。這名警衛看向車裡,用標準的英語說:「請問是瑞秋.朱小姐?」
「我就是。」瑞秋從後座揮了揮手。
「歡迎蒞臨,朱小姐。」警衛微笑地說:「沿著這條路開過去,靠右行駛。」他告訴司機該怎麼走後,便走回去開門示意他們前進。
「阿啦嘛,你們知道剛才那個男的是誰嗎?」裴琳的馬來籍司機轉過頭,露出些微敬畏的表情。「誰?」裴琳問。
「他是廓爾喀兵(Gurkha)!他們是世界上最驍勇善戰的軍人,我以前在汶萊常看到他們。
汶萊蘇丹只僱用廓爾喀兵做他們的私人保衛隊。到底這個廓爾喀兵在這裡幹嘛?」車子繼續往前開,駛上一個稍微隆起的小丘,兩旁都是密密麻麻修剪的樹籬。接著車子輕輕轉了個彎,他們看見另一道柵門。這次是一道鋼筋大門,緊鄰一個現代的警衛室建築。當大門靜靜向兩旁敞開時,
瑞秋看見另兩名廓爾喀兵從警衛室的窗戶向外看。前方出現另一條冗長的車道,上頭鋪著柏油路。車子駛過路面壓在鬆動的灰色小卵石上發出喀啦喀拉的聲響,在草坪後方出現一條兩旁種著棕櫚樹的大道,將起伏不平的草地一分為二。車道兩旁大概種了差不多三十棵棕櫚樹,整齊地排不知是誰在每棵棕櫚樹下裝上矩形燈罩,裡頭的蠟燭早已點上,好似燈火通明的哨兵在前方帶領著路。
當車子沿著車道往前開時,瑞秋驚奇地看著明亮的燈罩和四周修剪整齊的草坪。「這是什麼莊園?」她問裴琳。
「我不知道。」
「這裡是一個住宅群嗎?看起來我們好像開進地中海俱樂部度假村一樣。」
「我也不確定,我不知道原來新加坡有這樣的地方,感覺我們甚至不在新加坡似的。」裴琳驚訝地說。眼前的景象讓她想起在英國去過的莊嚴鄉村莊園,像是查茨沃斯莊園或布倫海姆宮。車子轉過最後一個彎後,瑞秋突然倒抽一口氣,抓住裴琳的手臂。遠方出現一座燈火輝煌的豪宅。車子越開越近,這座豪宅的宏偉壯麗就越顯真實。這不是一棟房子,反倒像是一座宮殿。前方的車道停滿了車子,幾乎每一輛車都很大且是歐洲進口的─賓士、Jaguar、雪鐵龍(Citroën)、勞斯萊斯,大部分都貼有外交標記並插著國旗。一群司機在車後面漫步抽著菸。站在大門門口,身穿白色尼龍上衣和寬長褲,頂著一頭蓬亂頭髮,一臉擔憂地把雙手插在口袋裡的人正是尼克。
「我覺得自己像在作夢,這不是真的。」裴琳說。
「噢,裴琳,這些人到底是誰?」瑞秋緊張地問。
這還是裴琳生平中第一次,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她突然狠狠地盯著瑞秋,然後用極輕的音量說:「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但我可以告訴妳一件事─這些人比上帝還有錢。」
14.8*21公分


-500x500.jpg)
-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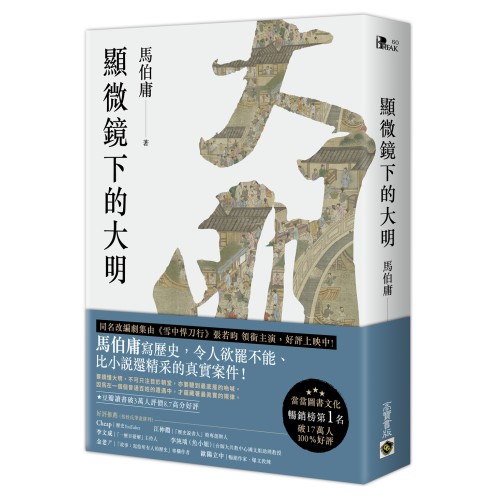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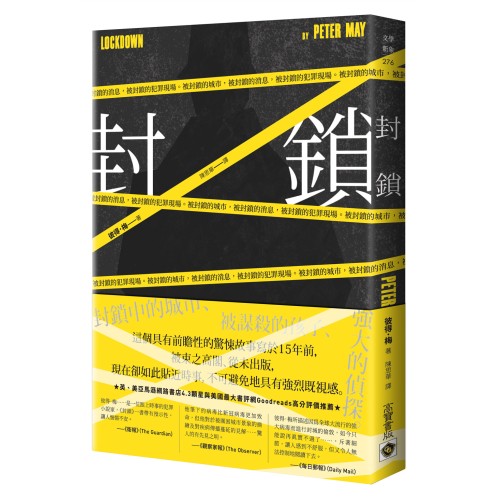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