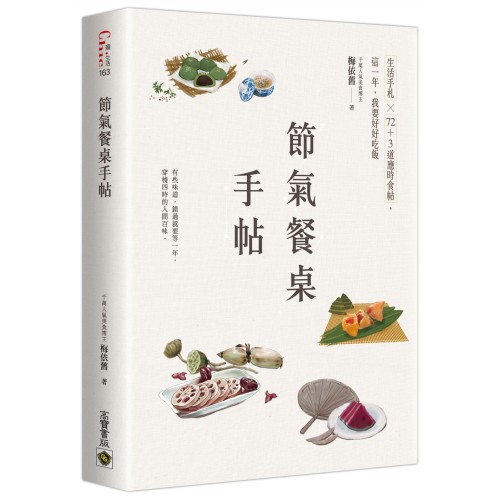-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大唐風物誌╳道家玄學╳歷史懸疑探案,
作者歷時三年精心創作,繼《永徽迷局》,再創歷史懸疑新風潮!
「乾坤反轉……冤命五道……解此連環……方得終兆……」
清冷孤傲的鬼手畫師孫道玄╳聰慧靈動的法探少女薛至柔,
在一次次的輪迴中,不斷追尋著懸案的線索與真相,
他們能否攜手揭開讖夢輪迴的祕密,破解錯綜複雜的連環之局?
薛至柔提著紅紙燈籠照著女子的屍身,
舉到頭面時,忍不住嚇了一跳──
在燈籠紅光的照耀下,這女屍的頭幾乎全是紅的!
薛至柔暗中深入調查,找出了連大理寺也未曾發覺的關鍵線索──
負責看管北冥魚的宮人,兩邊腳踝都有著詭異的傷痕,會是什麼凶器造成的?
凌空觀尚未倒塌的鐘樓上,印著兩排炭黑色的嬰兒腳印,這些痕跡又是怎麼來的?
薛至柔已經察覺,即將發生的第三起案件恐怕涉及大唐邦交,
但她萬萬沒料到,凶嫌竟然膽敢將黑手伸到幾百里之外,
在貞靜將軍樊夫人的眼皮底下,將相關人士殺害。
萬國朝會將近,這潛伏在連環懸案背後的凶手,到底有何目的?
【讀者燒腦推薦】
.沒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能看見薛訥、樊寧再次登場!薛至柔完全繼承他們的智慧與膽識,在層出不窮的連環案件中,屢屢破解凶手精心設下的陰謀。劇情緊湊,讓人欲罷不能,毫無疑問是今年度最讓我驚喜的歷史懸疑小說!
.作者的文筆優美動人,字裡行間有著詩詞韻味,將大唐盛世描繪成一幅瑰麗的畫卷,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的眼前,結合高潮迭起的連環謎案,讓人沉浸其中,捨不得把書放下來!
第二十一章 青絲繫禍
幾乎沒有片刻的猶疑,李隆基便頷首同意,帶薛至柔趕向了皇城南的鴻臚客館。
此事牽涉邦交,影響比薛至柔意料中更大,甫一拐進鴻臚寺的巷子,就見車馬來回,只是圍觀的人雖多,卻無人敢高聲言語,只有切切私語聲,更顯得客館內外氣氛詭譎。
薛至柔隨李隆基下了車,穿過裡三層、外三層看熱鬧的人,終於步入了客館。其內氛圍更是劍拔弩張,幾名新羅人圍著典客署令討要說法,說到情緒激動處,甚至以手不住點戳他的心口,極其無禮。
典客署令在鴻臚寺算是要職,品階卻不高,只有從七品下,身居其職之人年紀不大,看似只有二十出頭,卻有傲骨,面對對方的咄咄逼人,他始終保持風骨,不進不退,禮貌持重。
薛至柔瞬間想到了自己的父親,聽母親說,他初入仕時候也是這樣,雖口訥不擅言,原則事卻是寸步不讓。她忍不住開口,用新羅話說道:「既然事情還無定局,你們何故圍著典客署令要說法?等查出與我們唐人無關,你們可要向他致歉?」
新羅人一怔,紛紛向薛至柔看去,見來人是個身量都沒長齊全的毛丫頭,才想回嘴,再一撇她身側那器宇軒昂的男子,登時住了口。
李隆基示意典客署令:「聖人有令:限三日內查明真相,還武駙馬清白。本王特請了幾位行家到此,且由你與新羅使臣帶著,在這客觀內調查一番。新羅使臣何在?」
典客署令叉手稱是,四處張望,卻不見新羅使臣的人影,正納悶之際,一約莫五十上下的男子從人群外大步趕來,他面露愧色,操著熟練的中原官話道:「見過臨淄王,下官全洪,新羅使官。不知殿下駕臨,方才如廁去了,實在是……」
「這些便不必說了,」李隆基注意到大門藝帶著幾個人來到了門口處,招手示意他們過來,「我的人到齊了,可否查看下出事的房間?」
「好說、好說,殿下這邊請!」全洪說著,帶眾人穿過迴廊,走上木梯,來到新羅驛館二樓的一個房間內,「這崔湌是我新羅重臣崔沔之子,幾個月前才到長安城來求學,才辦了學籍沒幾日,哪知人就這麼沒了……」
薛至柔個子小,跟在最後走了進來,只見這是個套房,內外兩進,中間由拉門隔開,大的是起居室、臥室,小的裡面則擺了個大大的木質澡盆、恭桶與各種洗浴之物。
起居室裡散落著各種衣衫雜物,頗為雜亂,像是遭過賊。正對床榻是一扇支摘窗,面向大路,支起來容不下一拳通過,窗外亦無任何可以攀爬、落腳之處。
薛至柔回到房門口,仔細看看那被撞開的門扉,應是今早有人來找那崔湌,許久無人應聲,推測出他出了事,方找人撞了門。門板上有明顯撞擊痕跡,糊櫺紙碎爛,門閂卡扣也被撞脫,門框固定卡扣處的木頭起了刨花,如此看來,應當是從內緊鎖無疑。
薛至柔忍不住蹙眉思量,這房間在昨晚崔湌上鎖後,確實成了一間密室。
如此說來,武延秀對他的拳打腳踢便成為了崔湌死前最後一次受到外力攻擊,雖相隔數個時辰,但也並非絕無可能。薛至柔在遼東前線多年,知曉外力擊打臟腑出血或破裂,確實有可能在數個時辰後導致人死亡;抑或是擊中心門,導致胸痹,也會令人死亡。如此看來,武延秀確實有嫌疑,新羅人又不許仵作開腹驗屍,實在棘手。
薛至柔心思煩亂,攏了攏鬢旁的碎髮,盡量讓自己保持冷靜。她其實能夠理解,為何性情溫良的武延秀昨日會因為一句「綠帽駙馬」而動怒。他雖是則天皇后的侄孫,但自小過得不算太平,及冠後,又因為容貌俊美被則天皇后送去突厥聯姻,被對方嫌棄不是李唐宗室而拒婚。單一拒婚便罷,他們甚至將武延秀扣留在突厥六、七載,不得重回大唐。最後還是則天皇后命唐將沙吒相如領兵二十萬迎擊突厥,他才被放回朝,後迎娶了喪夫的安樂公主為妻。
薛至柔曾聽薛崇簡說,他覺得武延秀早就喜歡安樂公主,卻被則天皇后送去了突厥,再回來時,安樂公主已嫁給了他的堂兄武崇訓。其後武崇訓過世,他才終得娶了安樂公主為妻。可安樂公主酷愛俊美的少年,多年間傳聞不少,武延秀心中只怕多有不痛快,故而才會因為那句「綠帽駙馬」下手打人。
無論怎樣,真相遠比人情重要。
薛至柔走到起居室,看著滿地凌亂的衣衫,問全洪道:「這些都是崔湌的衣服嗎?可是破門而入時便在這裡?」
「是,確實如此。出了人命案子,下官自然不敢擅動房中之物。」
薛至柔心想,難道崔湌臨死之際,還曾努力尋過什麼東西?若真如此,又會是什麼?與他的死會有關聯嗎?抑或說,假如凶手另有其人,且有辦法進入這房間,難道正是為了圖謀某件物品才殺人嗎?
薛至柔的問話亦引起了同行者的警覺,一人問道:「可曾清點過崔湌的隨身物品?可有遺失?」
「已找他相熟的朋友清點過了,隨身之物並無遺失,而且他的錢袋就放在案上,位置十分顯眼,裡面錢很多,好端端放著呢。」
眾人聽罷,低聲議論不休。
李隆基示意眾人噤聲,又問全洪:「死者停靈何處?帶我們前去一觀。」
鴻臚客館之後有一方地窖,原是夏日給果蔬保鮮的地方,此時卻存著崔湌的屍身。那全洪打開了門後,自行躲到了一旁,估摸是怕看死人。薛至柔並不理會他,掀開屍身上的白布,只見那崔湌雙目緊閉,面色發白,沒有什麼明顯的傷處。不過,死者身上的一個不同於昨日的特徵,立即引起了薛至柔的注意,她忙轉向李隆基:「殿下,你看,他怎的沒了頭髮啊?」
李隆基亦是困惑,轉向典客署令:「昨日有何人對他行了髡刑?」
全洪上前兩步,待明白他們所指,他哈哈一笑:「殿下有所不知,這崔湌先天少髮,連髮髻都梳不起來,所以平日裡,都把頭髮剃光後佩戴義髻。不光是他,包括他的父親、祖父,都是如此。不過,此事在新羅人中知曉的人並不多,畢竟事關家族尊嚴嘛。」
薛至柔不由得以手扶額,武延秀若是知道這事,完全沒必要打他,只要把他的義髻扯下來,就足以懲治他的壞嘴了。
不過萬事沒有如果,木已成舟,人已死透,再也沒有什麼後悔藥。眾人仔細查看了死者,確實如先前所報的,除了被武延秀打過的地方之外,周身別無外傷。
薛至柔不由得嘆了口氣,感覺一切又回到了原點,而自己竟找不到任何能夠翻案的證據。其他人亦是如此,眾人商議後,決計去尋駙馬都尉武延秀,好問問昨日的具體情況。
薛至柔請辭道:「殿下,昨日打人時我在場,就不去找武駙馬了。若是殿下允許,我便自己在這轉轉,再尋尋線索。」
李隆基微微頷首,轉向大門藝:「勞你在這裡陪著至柔罷,她小小年紀,獨自一人不大方便。」說罷,李隆基帶著其他幾人出了地窖,那全洪快步跟著相送,不再搭理薛至柔與大門藝。
兩人也出了地窖,繞著鴻臚客館溜達。薛至柔像是想到了什麼,問大門藝道:「哎?大兄,說起來你也應當住在這客館罷?」
「只有初到長安那半年住,」大門藝笑道,「這鴻臚客館裡哪裡來的人都有,不免有些雜亂,我阿爺便在長安給我買了宅子,距離三郎府上也近,往來更方便些。」
薛至柔應道:「是啊,各國之人住一起難免有些不便,也不是人人都會中原官話。」
「其實倒也不至於那般雜亂,基本上每個地方來的人都會住在同一棟,也更方便管束一些。只是妳也是打安東過來的,自然知曉,新羅、百濟本就與我們渤海靺鞨不大和睦,縱使不住在同一棟,這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總還是有些尷尬。」
薛至柔對這些事沒興趣,沒有接腔,而是被某處傳來的氣味吸引。她吸了吸鼻子,詫異道:「嚇,別是哪處著火了,怎的有這樣大一股糊味啊?」
大門藝也嗅到了這股味道,兩人像是兩條巡邏的獵犬,一路嗅著,尋到會館後院一間無人看守的伙房。薛至柔步入其中,只見門後藏著一只敞口的火爐。爐璧已沒了溫度,但仍散發出嗆人的氣味,爐內殘餘不少未燒盡的木炭與炭灰。
「這是怎麼回事?大夏天的竟還有人用爐子?」薛至柔問大門藝道。
大門藝卻不以為,十足篤定道:「應是哪個饞嘴子昨晚用來吃炙豚肉了罷?畢竟無論是新羅還是我們靺鞨,都愛吃炙豚肉。只要將豚的里脊切成片,往這爐子裡放上炭火,把這鐵絲圍的網屜架在炭火上一烤,再配上燒酒,那叫一個香!」說著,他發覺有個細鐵絲圍成的圓形網屜靠在牆上,更覺添了佐證:「妳看,我說什麼來著?」
薛至柔走上前,扒頭看了看那鐵絲製的網屜,其上黑糊糊的一片,看來應當確實是在火上炙烤導致,卻未看到什麼油膩,一個奇異的想法在她腦中升起。
薛至柔起身便往外跑,大門藝喚她不及,連忙追去。
薛至柔先是來到客館的一層,發現各個房間的布局與二樓完全一致,仔細嗅嗅,有股沉沉的酸氣。她便又回到二樓崔湌的房間,將所有物品再度看了個遍,嘴角終於微微勾了起來,對大門藝道:「大兄,勞煩你,快去通知臨淄王殿下,就說武駙馬確實是冤枉的,我已查明白凶手和作案手法了,請他趕緊遣一隊飛騎營士兵來,將客館內外封鎖,館內所有人暫時待在自己房間內,有任何人攜帶行李外出,都要驗明行李內容。」
「啥?」大門藝十足吃驚,愣愣半晌沒有應聲。天知道,他可是抱著帶小孩子玩的心態在這裡陪著薛至柔,她難道還當真會查什麼案子不成?
他這反應惹得薛至柔好氣又好笑,讓她想起小時候偶時隨母親外出,某些將領聽母親說起行馬打仗時的神情。母親從不屑於解釋,她亦是如此,只是肅然了俏麗稚嫩的面龐,認真說道:「若是動作慢了,放跑了凶嫌、丟了證物,你……」
果然,大門藝聽了這話,心道此時還不是死馬當活馬醫,就算混鬧出了過失,大家一起挨皇帝的罵就是了,轉身便出了門,牽出馬飛快疾馳出了宮城。
尺寸(公分)14.8*21*2.2cmcm
開本 25
頁數 344
第二十二章 萬緒千頭
第二十三章 撥雲見日
第二十四章 鬼燈一線
第二十五章 為山止簣
第二十六章 七月流火
第二十七章 魯魚亥豕
第二十八章 一差二錯
第二十九章 鳥入樊籠
第三十章 混沌重渡
第三十一章 山重水複
第三十二章 棋輸一著
第三十三章 天機道破
第三十四章 福無雙至
第三十五章 如臨深淵
第三十六章 新仇舊怨
第三十七章 秣馬厲兵
第三十八章 神工鬼斧
第三十九章 虎尾春冰
第四十章 救焚拯溺
第四十一章 圖窮匕見
第四十二章 水落石出
第四十三章 不堪前塵
第四十四章 請君入甕
第四十五章 終章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