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我已經沒有故鄉了,妳就是我的故鄉。
★ 愛奇藝熱播動畫同名原著小說!
★ 年度十佳網路文學潛力新人 七英俊 腦動清奇之作!劇情跌宕,令人捧腹大笑的反套路穿越文!
★ 當當網長期在榜,五千名讀者五星好評,喜馬拉雅有聲書評分9.8,豆瓣書評8.1高分!
★ 穿越一代妖后 庾挽音×穿越一代暴君 夏侯澹,穿越者相遇,如同他鄉遇故知,先來一桌小火鍋,再來一碗豪情酒(讀者:看到都餓了)。
──「皇命易位,帝星復明。熒惑守心,吉凶一線。」
難道砲灰配角們如何掙扎,都註定無法贏過主角光環?
夏侯澹躲過了邶山上的行刺,推翻了太后黨,
庾晚音找到了對抗旱災的農作物,收攬未來棟梁進入朝堂。
端王的陰謀仍沒有停止,而謝永兒與庾晚音既然無法為他所用,便棄之、毀之,
他要坐上皇位,哪怕成王之路上血跡斑斑。
夏侯澹為太后送葬的路上,註定會有一場刺殺,
他自知逃不了,也不想再逃了,
只期望庾晚音性命安穩,她能成一代明主,
只可惜他們相遇太晚,相處太少。
在這暗無天日的宮中,殺伐如常,毒已入骨,他的命數已定……
在穿越之前,庾晚音當了多年的社畜,
面對老闆與客戶的百般刁難都能游刃有餘。
她不信命運該當如此,
社畜的憤怒,足以扭轉一切──
第十九章 無解
練了球的小美女們以為終於摸准了庾晚音的喜好,當即在御花園中支起了球桌,以不畏嚴寒的奮鬥精神打起球來。
幸而天氣晴冷,無風無雪,打著打著也就熱了。
庾晚音當時只是隨口一說,其實她根本不會乒乓球,更何況這繡球基本可算是一項新運動。但大家菜得半斤八兩,加上拍馬屁的有意放她水,倒也有來有回。
場面一時虛假繁榮。
幾輪下來,或許是大腦開始分泌多巴胺了,又或許是宮鬥場景成功進化到了公司團建,庾晚音久違地渾身鬆快,漸入佳境,甚至連旁人的叫好聲突然弱了下去都沒察覺。
直到漏接一球,她笑著轉身去撿,才發現繡球滾落到了不遠處的一雙腳邊。
那雙腳上穿著朝靴。
庾晚音:「……」
夏侯澹俯身拈起那繡球,「這是什麼?」
眾妃嬪行過禮後低頭站在一旁,大氣不敢出,全在偷看庾晚音的反應。
皇帝昨夜發瘋、庾妃今早封后——這兩則新聞之間,到底是個什麼邏輯關係?無數顆腦袋絞盡了腦汁都沒想明白。
其實能在這樣一本水深火熱的宮鬥文裡存活到今日的人,多多少少都領悟了一個道理:在這活下去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作死。無數個慘烈的先例證明,鬥得越起勁,死得越早。
但這條規則對庾晚音不適用。
庾晚音入宮以來,扮過盤絲洞,也演過白蓮花、藏書閣裡的大才女、不會唱歌的傻白甜、不諳世事吃貨掛、怒㨃皇帝清流掛、淒風苦雨冷宮掛……恨不得把每一種活不過三章的形象挨個扮演一遍,各種大死作個全套。
以至其他人有心學一學,都不得其法,因為她們至今分析不出皇帝吃的是其中哪一套。
或許其精髓就在於這種包羅萬象的混沌吧——有人這樣想。
可如今她當了皇后,正值春風得意時,總該流露出一點真性情了吧?
這帝后二人如何相處,直接關係到前朝、後宮日後的生存之道,必須立即搞清楚。
庾晚音想不出更好的答案,「乒乓吧。」
「乒……」夏侯澹狐疑地看了那繡球一眼,眼中寫滿了拒絕。
庾晚音擺了擺手,示意他別挑刺了,「能打的能打的。」說著接過球,示範著發了一球,對面小美女不敢接。
夏侯澹抽了口氣,「妳這拍都……」沒拿對。
庾晚音:?
好傢伙,還是個行家?
她用眼神問:你要加入嗎?
夏侯澹搖搖頭,溫聲道:「皇后累了嗎?」
庾晚音聽出他是有事找自己,忙道:「確實有些累了,今日就到此為止吧,改日再來。」
對面小美女回過神,囁嚅著應了:「娘娘保重鳳體。」
等庾晚音坐上龍輦去遠了,眾人茫然地面面相覷。
別說如何相處,她們甚至沒看懂那兩人是如何交流的。
用神識嗎?
龍輦上,庾晚音貼在夏侯澹耳邊呼出一口白霧,「怎麼了?」
夏侯澹道:「邊軍有人偷偷動了。」
「哪一邊?」
「三邊都有,詳細人數還未查明。看來夏侯泊等不住了。」
庾晚音在他開口之前已經隱隱猜到了。
此事他們早就商討過,也想到了一旦夏侯澹穩固住中央勢力,端王只能去借邊軍。如今三軍皆被他買通,只是應了最壞的一種設想。
所以她平淡地接了一句:「那我們也抓緊吧,趁著他的援軍還沒到。」
「嗯,我跟蕭添采說了,太后的吊命方子可以停了。」
庾晚音問:「那她還能苟活幾天?」
夏侯澹委婉道:「蕭添采會停得比較藝術。」
庾晚音:「……」
她轉頭望了一眼。
夏侯澹握住她的手,「在看什麼?」
「沒什麼。」冬日的陽光總是格外珍貴,庾晚音忍不住對著御花園的花草多望了一下,隱隱預感到那「改日再約」的下一次乒乓球賽,怕是遙遙無期了。
「浮生半日閒,果然是偷來的。」
※
蕭添採辦事十分俐落。
翌日深夜,庾晚音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安賢在門外顫聲道:「陛下,太后不好了。」
這聲通傳如同發令槍響,庾晚音倏然清醒過來,轉頭看向身邊的人。
夏侯澹也正望著她,輕聲問:「準備好了嗎?」
庾晚音點點頭,道:「走吧。」
為了表達悲痛,安賢今日的唱名聲格外鬼哭狼嚎一些:「皇上駕到——」
夏侯澹攜著庾晚音的手走下了龍輦。三更半夜,冷風刺骨,凍得庾晚音一個激靈。
有侍衛跟了上來,在他們身後低聲道:「尚未發現端王的人。」
暗衛已經在太后寢宮周圍蹲伏多時了。只要太后一斷氣,端王隨時可能行動。所以從現在開始,他們就進入了一級戒備狀態。
夏侯澹不著痕跡地微一點頭,走進大門。
正屋裡已經跪了一地宮人,動作快的妃嬪也火速趕來跪好了,一個個面色慘白,端出一臉如喪考妣的神態。但眼淚尚未醞釀出來,說明太后還剩一口氣。
庾晚音跟在夏侯澹身旁越過人群,走向裡屋,不經意地瞥了眾人一眼,微微一愣——好些人都在偷看她。
更確切地說,是在偷看她的肚子。
那探究的目光近乎露骨,庾晚音本能地感到不適,舉起袖子擋了一下。
於是更多的目光直勾勾地射了過來。
庾晚音:?
幾個老太醫從裡屋迎了出來,後面跟著作為學徒的蕭添采,眾太醫照著流程往夏侯澹跟前一跪,老淚縱橫道:「老臣無能,老臣罪該萬死啊……」
夏侯澹也嚴格遵照流程,一腳踹開為首的老太醫,急火攻心地衝了進去,人未到聲先至:「母后!母后啊!」
裡間空氣混濁,彌漫著一股不妙的味道,由排泄物的臭味與死亡的陰冷氣息混合而成。
床上的太后已經換上了壽衣,形容枯槁,四肢被人擺放端正了,雙手交疊於胸前,僵屍般直挺挺地躺著,一雙眼珠子幾乎暴突出來。
小太子跪在一旁角落裡,縮成一團,幾乎像個斷了線的傀儡,走近了才會發現他在瑟瑟發抖。
夏侯澹道:「啊!」他聲音大得離譜,似乎是為了確保外面的人都能聽見,「母后且安心,兒子來了!」
庾晚音:「……」
她今日算是見識到了演技的巔峰。
夏侯澹居然能一邊語帶哭腔,一邊對床上之人露出一抹飽含惡意的微笑。
太后被他激得整個人抽搐起來,卻只能發出「呃啊啊」的聲音。
夏侯澹一屁股坐到床沿上,貼心地伸手幫她掖了掖被角,「兒子都明白、都明白。」
四目相對,夏侯澹的眼前浮現出初見之時,那雍容華貴、不可一世的繼后。她殷紅的指甲劃過他的面頰,刺得他眼皮直跳,卻不敢躲閃。
當時的他如同一隻待宰羔羊,唯一能等待的只有他人的垂憐。
若說她在這十餘年裡真正教會過他什麼,那或許就是:不要等。
太后指甲上的蔻丹早已剝落得一片斑駁。她瞪著夏侯澹抽了半天,每抽一下,出氣就更多,入氣則更少。
夏侯澹問:「什麼?小太子?」他朗聲道,「母后不必擔心,朕必然會好——生——照料他。」
借著床帳遮擋,他對著太后比畫了一個抹脖子的手勢,笑得更喜慶了。
太后:「……」
夏侯澹以為她這一下就該氣死了,她卻仍舊萬分艱難地喘著氣,無神的眼睛直對著他,嘴唇微微嚅動。
奇怪的是到這境地,她的眼中反而不剩仇恨了,殘存的只有不甘。
夏侯澹揣摩一下此時她的走馬燈裡能閃過什麼畫面,愣是沒想出答案。
她沒有愛人——她親口告訴過他,她今生最恨的就是先帝。
她沒有情人——這麼多年她連個裙下臣都沒養過。
她也沒有子嗣——早在她爬上后位之前,老太后就奪去了她這輩子受孕的可能。
或許從那時開始,她一生所求就只剩權柄了。
弄死老太后、熬死先帝、控制夏侯澹、操縱小太子……何必愛世人?何必索求愛?與人鬥,其樂無窮。夏侯澹毫不懷疑,她即使成功弄死了自己與端王,也會不知疲倦地繼續鬥下去,直到生命盡頭。
可惜,她輸得太早了。
太后如同垂死的魚一般猛烈掙扎起來,口型接連變換,發出含混的聲音。
夏侯澹不願俯身去聽,就偏了偏耳朵,不耐道:「什麼?」
太后突兀地笑了一下,她慢吞吞地說了幾個字。
夏侯澹頓了頓。
太后擱在胸前的手顫顫巍巍地抬起一寸,又猛然跌落下去,頭偏到一旁,再也不動了。
死寂。
太醫在一旁聽著不對,跪行過來撩開床帳,象徵性地把了把脈,又翻了翻她的眼皮,顫聲道:「陛下……陛下……」
夏侯澹維持著坐姿一動也不動。
跪在床尾的庾晚音等了十幾秒,莫名其妙,只得起身走過去,拉他站了起來。
夏侯澹這才像是被撥動了某個開關,氣沉丹田,哭出了第一聲:「母——后——」
外頭收到信號,立即跟上,此起彼伏地號起喪來。庾晚音從裡屋聽見,只覺聲勢浩大,有男有女,似乎是大臣們也趕到了。
不知道端王來了沒。
她一邊敷衍了事地跟著乾號,一邊在腦中又過了一遍暗衛藏身的位置。
夏侯澹自然不能哭一聲就算完事,還替太后闔上眼睛、整理壽衣,做戲做全套。
一旁趴著的小太子也開始抽噎起來。他或許是整間屋子裡唯一一個真哭的人,很快哭得涕泗橫流、傷心欲絕,渾身抖得像是打起了擺子,邊抖邊朝床邊爬來,似乎還想看太后一眼。
庾晚音低聲問夏侯澹:「她剛才留了什麼遺言?」
夏侯澹轉頭看向她,神色有些木然,「她說她在地下等我。」
庾晚音心裡「咯噔」一聲,從足底泛起一股陰寒之氣,「什麼玩意,死到臨頭了還只顧著咒人……」
她在餘光裡瞧見小太子爬到了近前,下意識地瞥了他一眼。小太子正望向夏侯澹,一張小臉繃得太緊,五官都變了形,整個人連呼吸都止住了,彷彿一個行將爆炸的氣球。
就在這一刹那,庾晚音忽然心頭一緊。憑著生死間練出的直覺,她的身體動了。
她猛地撲向夏侯澹,一把將他撞開——
與此同時,小太子揚起手臂,袖中騰起一陣紅霧,兜頭灑向夏侯澹,卻被庾晚音擋去了大半——
庾晚音預期的是匕首、暗器,萬萬沒想到會是這樣的東西,一時不防吸入了一口,猛地嗆咳起來。
夏侯澹被她推出兩步,呆了一瞬,立即掩住口鼻,衝回來將她拉走,回身狠狠一腳,正中小太子心口。
小太子整個人被踹飛了,跌到地上吐出一口血。
庾晚音跌跪在地,咳得上氣不接下氣。夏侯澹伸手在她衣髮上一抹,指尖沾滿了紅色的粉末。
暗衛已經控制了室內所有宮人與太醫,又將地上的小太子也制住了,「陛下,此地不宜久留,請先暫避……」
夏侯澹大步上前,一把掐住小太子的脖子,「解藥。」
小太子放聲尖叫。
動靜傳出裡屋,外頭敬業的哭聲一停。
夏侯澹的五指漸漸收緊,將那尖叫聲硬生生掐斷,「解藥。」
小太子掙扎起來,一張臉漲成了紫紅色。暗衛見勢不妙,試圖阻攔,「陛下息怒!」
夏侯澹理也不理,掐人的手上青筋暴突,眉間躥起一股黑氣。
庾晚音終於緩過氣來,居然沒有其他不適之感。她轉頭一看,見小太子眼睛都翻白了,連忙去掰夏侯澹的手,「快停下,我沒事……」這一掰竟未掰動,她慌了起來,湊到他耳邊提醒,「所有人都在外面,你想當場坐實暴君之名嗎?」
夏侯澹充耳不聞。
庾晚音定睛一看,嚇得呼吸一窒——夏侯澹的眼球都充血了,面目猙獰,宛如修羅。
他從前發瘋的時候都沒有露出過這副面貌。
庾晚音忽然想起那紅色粉末。那玩意,夏侯澹剛才也吸入了一點吧?
她強壓著恐懼指揮暗衛:「幫忙救太子!」
暗衛猶豫著不敢動。
庾晚音啞聲催促:「快點,我們還要問解藥!」她自己吸入的紅粉比夏侯澹多得多,此時就像往體內埋了顆定時炸彈,不知何時就會出現症狀,只能趁著神志清醒,盡一切可能穩住局面。
暗衛一咬牙,並指一戳夏侯澹臂上某處,戳得他手臂酸麻,被迫鬆開了手。
暗衛剛剛拉開太子,夏侯澹就嘶聲道:「殺了他。」
暗衛道:「陛下……」
「殺了他!」夏侯澹口中發出一聲野獸般的怒吼,一拳揮了過去。暗衛不敢擋他,狼狽不堪地避過了。
夏侯澹撲過去奪他的劍。
暗衛繞柱走。
夏侯澹伸手入懷,掏出了槍。
所有知道那是何物的人都瞳孔驟縮——
對準那暗衛的槍口被一隻手握住了。
庾晚音渾身發抖,「夏侯澹。」
夏侯澹下意識地望向她,在看到她眼眶裡的淚水時幾不可察地凝滯了一下,那雙黑暗混沌的眸中,一團風暴止歇了幾秒。
庾晚音其實理智都快崩潰了,五指順著槍身慢慢攀去,摸到他手背的皮膚,說不清誰更冷,「晚上吃小火鍋嗎?」
夏侯澹頓在原地。
就在這一頓之間,庾晚音輕聲道:「敲暈他。」
暗衛這次沒有猶豫,一記手刀劈倒了皇帝。
庾晚音舉目四顧,太后已死,皇帝中毒,太子半死不活。
她又轉頭看了看正屋的方向。臣子與宮人還在低低哭著,但聲音很輕,顯然在側耳傾聽裡面的詭異動靜。
室內的人全望著她。
庾晚音強行勾起嘴角,「陛下傷心過度倒下了,快扶他回去休息。太子情緒不穩,也需好生安撫。」
暗衛會意,架著夏侯澹和太子從後門走了。
庾晚音抬手從肩上掃落一把紅色粉末,攥在手心。
這玩意兒到現在都沒對她產生任何作用。她心中隱約有了個猜測,當下便對那些太醫與宮人笑了笑,「不必驚慌,一切照常吧。」
說著安撫的臺詞,那笑意卻是冷的。
她自己或許沒有察覺,但看在他人眼中,這新上任的皇后周身的氣勢已經不同以往。
那些人打了個寒顫,慌忙動了起來,有人搬來梓宮上前入殮,有人打掃一地狼藉。
庾晚音給蕭添采使了個眼色,將目光指向太后的屍首。
蕭添采若有所悟,躬身走到那碩大的梓宮邊,與宮人一道整理起太后的遺容。
尺寸(公分)14.8*21*1.89
開本 25
頁數 296
第十九章 無解
第二十章 決戰
第二十一章 吾妻晚音
第二十二章 故人重逢
第二十三章 黎明前的至暗寒夜
第二十四章 重掌河山
第二十五章 鳳棲於梧
第二十六章 以毒攻毒
第二十七章 大好春光
番外一 相逢何必曾相識
番外二 人物小傳
番外三 小段子
感謝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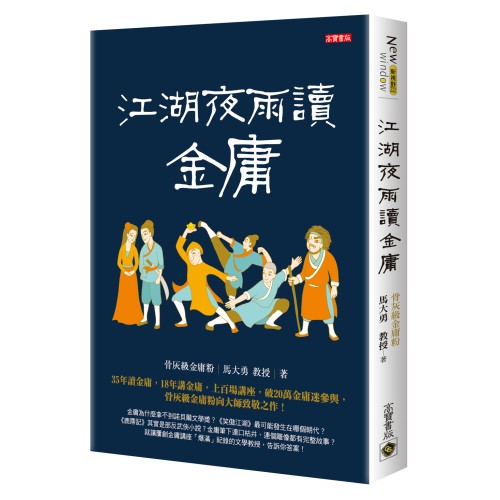
+書腰_立體書-500x500.jpg)
印簽_立體書-建檔更新-500x500.jpg)
+書腰_立體書_建檔-500x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