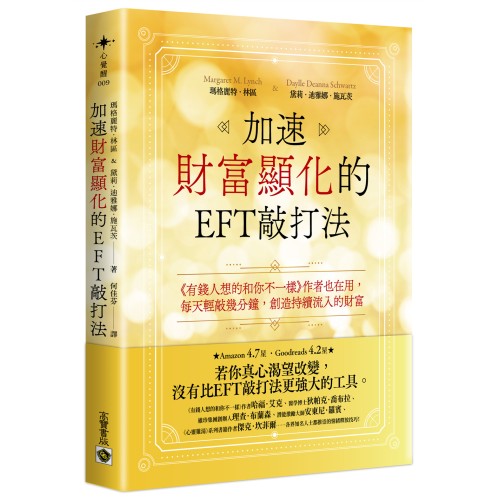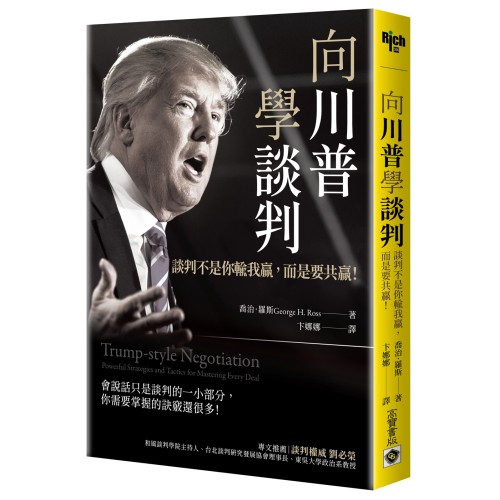會員限定
故事洗腦術:從商業行銷、形象塑造到議題宣傳都在用的思想控制法則
NT$363
NT$460
-
作者強納森.歌德夏 Jonathan Gottschall
-
譯者蕭季瑄
-
ISBN9789865065294
-
上市時間2022-09-28
-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你喜歡聽故事嗎?
一個吸引人的好故事可以建立文明世界,
也很可能讓人類社會就此毀滅……
本書帶你窺探故事背後席捲人心、讓人欲罷不能的黑暗秘密
該如何影響他人?如何賺到他們的錢?如何向他人誇耀生命的美好?如何讓其他人和我有一樣的世界觀?如何逗他們笑、讓他們喜歡我?如何贏得他們的選票?如何讓所有人團結一心?如何改變世界?只要說一個好故事。
人類天生就愛說故事。我們是說故事的動物,故事是社會的起源。但是,故事也具有一個長期被我們忽視的黑暗力量。
近幾十年來,研究「說故事」的這一門科學逐漸興起,讓我們意識到「故事」既可以促進同情、理解、慈善、和平,但是也可以促進分裂、懷疑與仇恨。「說故事」就是隱性洗腦,它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毒藥,我們需要它,但又可能在不經意間被它損害。
故事的力量就是激起情緒,而情緒是人類作出決定時的關鍵因素。說故事的人是「暗中的宣傳者」,沒有什麼比故事更能奴役人類。
想要說服他人,用說故事的方式往往比說理更有效。故事的力量之所以這麼強大,是因為它可以不受理性的審查,並偷偷在聽者心中植入資訊與信念,進行隱性洗腦。新科技的發展讓人們更難以區分虛構與現實,掌握說故事的技藝,就掌握了指出真相與真理的權力。
歷史上每一個極權主義烏托邦的首條規則就是控制與壟斷「故事」,而社群軟體更讓人類逐漸離開一個共享真相的世界,進入一個夢幻世界。如今,每個人都是獨自盯著自己的螢幕,真相不是由最合理的證據所支持,而是由最精彩的故事所建構。
本書帶你探索心理學家、溝通專家、神經科學家與文學專家共同研究故事如何影響我們的腦,其結果顯示:說故事是繞開理性批判、控制彼此心智絕佳的方式。掌控與壟斷「故事」的人,就能夠讓別人失去理性,甚至改變他們的判斷。
從宣傳特定議題、塑造個人形象,到宗教、政治、資訊戰,在所有瘋狂行為背後,你永遠能找到一個誤導心智的好故事。
專業推薦
Lynn/三分鐘|行銷在學中創辦人
李白/街頭故事創辦人
李洛克/《故事行銷》作者
林長揚/簡報教練、暢銷作家
許榮哲/華語首席故事教練
歐陽立中/《故事學》作者
鄭俊德/閱讀人社群主編
(依姓氏筆畫排序)
各界好評
「強納森.歌德夏不僅是關於故事在我們生活中強大作用的最深刻思考者,而且還是一位活潑詼諧的作家。這本書提供了很多洞察力和許多樂趣。」
——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強納森.歌德夏就一個被忽視但緊迫的話題寫了一本引人入勝且深思熟慮的書:故事的陰暗面。他用清晰的散文和一系列引人入勝的例子,展示了我們與生俱來的編造故事的能力如何導致扭曲、瓦解和破壞。這本書是一個振奮人心的號召,呼籲我們採取行動變得更有同理心,並將敘事作為一種向善的力量。」
——丹尼爾‧品克(Daniel H. Pink),《未來在等待的人才》作者
「在這本具有啟發性和洞察力的書中,強納森.歌德夏向我們展示了為什麼危險的故事傳播得如此迅速,以及它們如何導致分裂和不信任。但我們講故事的本能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用,本書利用大量的研究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向我們展示如何阻止陰謀、偏執和錯誤信息。」
——約拿‧博格(Jonah Berger),華頓商學院行銷學教授
「這本引人入勝的書探討了故事的黑暗力量,認為它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毒藥——對人類生活是必需的,但往往是一種非理性和殘忍的力量。這本書具有挑釁性和原創性,讀起來很愉快——諷刺的是,強納森.歌德夏本人就是個講故事的人。」
——保羅‧布倫(Paul Bloom),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
「我們不斷地修改彼此的大腦,而我們使用的手術工具就是講故事。強納森.歌德夏在這部閃亮而精闢的著作中帶我們深入故事的世界:我們講述了什麼,我們如何接受,以及為什麼它對我們的世界如此重要。」
——大衛‧伊葛門 (David Eagleman),史丹佛大學神經科學家
「愛聽故事是我們的天性,但在享受故事之餘,請記得別太快陷入情境當中,先退一步思考與查證相關證據,可以避免自己被有心人士操弄。書中詳細介紹了許多故事洗腦的案例與原理,好好閱讀就能幫你練成真實之眼,快來為自己打造洗腦防護罩吧!」
――林長揚,簡報教練、暢銷作家
前言 千萬別相信說故事的人
不久前我去到一間酒吧,心想在裡頭肯定只能做些簡單的思考。當時我對世界的狀態很是絕望,也對這本書感到相當迷茫。我已經花了很長時間做研究及制定計畫。我寫了好幾百頁的筆記、好幾百頁的草稿,也嘗試了數種不同風格、但全數被打回票的書名。現在是二○二○疫情年的初期,我知道自己就要錯過截稿日期了,即便延期可能也於事無補。
當然了,大致上我很清楚這本書的主題。故事。各種故事—事實、小說、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怪誕的敘述。更具體地說,是關於故事以我們察覺不到的方式形塑我們心智的暗黑力量。而對此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以清晰的敘述線闡明兩千四百年前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學問、大西洋區恐怖的奴隸交易、中世紀引發恐慌的詭異洗腦術、匿名者Q(QAnon)和地平說理論的可怕崛起、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氾濫、深入瞭解世界上最優秀(最差勁)作家的藝術創作過程、虛擬實境的興起以及美國社會的兩極化,再加上我們的大腦與故事如何相互形塑的大量研究。
這全部都導向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此時此刻,人類似乎被故事給逼瘋了?
因此我坐進酒吧內安靜的角落,點了一大杯店內最便宜的波本酒。我戴上耳塞、將筆放在乾淨的紙巾上。我正等待酒精發揮效用,希望能改變我當前的意識狀態,再加上眼前的佈景,或許能夠改變我的創作習慣。我盯著紙巾一會。我隨手塗鴉。然後我又點了另一杯酒並四處張望。我先是看著一台靜音的電視裡播放以廚師為主角的實境節目。
然後轉向另一台電視,看著ESPN 兩個彪形大漢隔著桌子相互大吼。脖子再轉動一點,正好看到下一台電視內的新聞接檔甫結束的警匪劇。
那時候,我承認自己是來喝酒、而不是來思考的。但當我環視著酒吧,我發現酒精確實帶來了我所期盼的另個角度的世界觀。正常來說,當我們觀察一大群人時,並不是「真正」在觀察他們。我們會放大聚焦於某一部分的個體。或許是某個特別漂亮的人吸引我們的目光,讓我們觀察良久直到終於能別開眼神;然後我們又注意到了一個穿著特別有型或怪異的人;下一個人則特別高、矮、胖或瘦。我們的雙眼一再游移,掃過一個個偏離常軌的畫面。
總之這是我的看法。但那一晚,我能夠注意到整個群體,而非只是個體—是整片森林,不是樹木。人們假裝自身的行為多樣多變且不可預測,並為此自我感覺良好。但事實不然。人的行為是千篇一律的陳規,且可以預測。而酒吧內的所有人(除了某位又醉又悲傷的作者)都在做一模一樣的事。
以下是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他們的雙手在空中揮舞;他們的嘴巴開開闔闔;他們的脣舌靈敏且不間斷地移動;其中一些人發出顫音,其他人則咆哮著。我看到有個男人將手掌圈在一位女士耳邊,溫熱的氣息將螺旋狀的訊息傳送進她的腦海。女士的頭彷彿抽蓄一般猛地縮了回去。在她對著天花板發牢騷時,頸部內的血管收縮彈動。
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酒吧裡的所有人都在做這些事。桌旁的老顧客如此。服務生和調酒師也是如此。連電視裡的人也一樣——氣呼呼的前運動員、做作的新聞主播、扮演警察和搶匪的演員、推銷吸水抹布的人。我將視線轉回紙巾,用手指戳一戳揉捏過的耳塞。「這些人真是奇怪,」我寫道。
「他們為什麼在這裡? 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當然了,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正和朋友們相聚。他們試著和生命中所愛之人相處。或者跟我一樣,他們正透過輕微的絕望感治癒自己。但為什麼每當人們兩兩相聚時,總會歇斯底里地喋喋不休、表情千變萬化、雙手不停揮舞呢?
每一天,從早到晚,人們都穿梭在自己與他人吐出的字詞話語中。人的一生皆是如此——從嬰兒和母親最初的呢喃耳語到臨終前吐出的最後愛意之詞。只要人們相聚,無非是輪流出聲。就算自己沒有發表言論時,大多也是看著電視裡的人高談闊論或者像是閱讀本書一樣看著他人所寫的文字,也可能是聆聽播客或是低吟哼唱的樂音。
若你是研究人類行為的外星學者,且被要求點出一項最能代表人類的活動,你的答案可能是「睡覺」或者「工作」。但這只能表示你這個外星人一點也不了解人類。若你跟我一樣是地球土生土長的學者,你的答案應該會是「交流」。
然而,仔細一看,這些交流的內容大多都沒有意義。我曾經受邀口沫橫飛、比手畫腳地發表有效教學中說故事所扮演的角色,那個房間內擠滿了過去在核能發電廠工作的安全指導員。他們說的話非常重要。要是指導員們的用詞不夠精確且語序不對,災難則無可避免。
大多數的溝通交流都不若如此。通常我們談論的都是某個人那隻滑稽的狗、愚蠢的老闆或是令人失望的男友。酒吧電視裡的憤怒前運動員大吼著談論一位名叫羅布.格隆考夫斯基(Rob Gronkowski)的混血足球民族英雄—他到底該不該復出? 就連你們這位傷心酒醉的作者也坐在酒吧裡對著自己喋喋不休:他是不是很失敗啊? 有多少作家被自己的書給害死呢?
我盯著寫在紙巾上的問題: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來回掃視著這句話直到字母在眼前成了粗體字。我抬眼,看著屋內的人們起身坐下、前傾後靠、來回走動。感覺起來他們似乎都被話語的力量給推動著,仿若是受微風拂動(Sway)的樹林。
我在紙巾上寫了另一個字:「影響」(Sway)。
我稍微轉動一下紙巾,好從另一個角度審視這個字,然後在後頭加上一個問號:「影響?」我朝著整個空間皺眉了良久。
影響
我們生命中所有不曾倦怠的交流都有個主要目的,這個目的便是影響他人的思想—影響他人的想法、感受,最終影響他們的行為。無論我們於何時交談,都在用一些空虛且微不足道的話語試圖動搖他人,即便只是一點點,也都在以利己的方式重新安排這個世界。
除了影響他人,我們幾乎沒有為了其他理由呼吸、打字、歌唱,這個邏輯甚至也能套用在我們與自我的對話。雖然很難以科學的方法解讀內心的聲音,但很久以前心理學家就已經證實「自我對話在抑制衝動、引導行為以及監控目標進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
換句話說,自我對話是影響、形塑以及督促自己的方式。
在某些例子中,影響他人在交流中扮演的核心地位顯而易見。銷售員和政治人物的發言,顯然都是要說服我們買單,在我身處的酒吧之中此現象並不明顯,但仍是不爭的事實。雖然酒館內的對話內容通常都很微不足道,仍然能發揮顯著的效用:建立或維持人類發展中至關重要的社交聯繫。就連在飛機上和陌生人交談這種隨意的對話也可能反映了一種本能:想在對方殺掉我們或偷走我們的東西前與之成為朋友。
我們傾盡一生喋喋不休,因為我們作為溝通者的能力可以預測我們的影響力——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讓他人服從意願、而非臣服於他人的意志。請理解這些都不是必然,甚至大多都很馬基維利主義。所有那些有關智人的無聊論述指陳,正如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所說,我們也是個「相當親切的物種」。2
我們日復一日與朋友及陌生人互動,可說是無可比擬的友善,或者至少是相當中立的行為。這種親切代表我們為了他人的利益奮力地想影響他們,至少不亞於我們試圖利己的目的。而人類這個曾經溫馴的物種統領地球的一大原因,即是複雜的語言使我們能夠比其他動物更有效地相互合作。3
簡單地說,我們想要發揮影響力,目的是為了共生,而非寄生。
也許你覺得這個有關影響力的言論很有趣。也許你覺得這顯然是個老套之詞。酒吧帶來的眩暈感一消失,這個觀點令我感到既老套又有趣。但是,交流的影響力這個簡單的觀點,只是說故事的目的更激進三段論的第一小步。
影響他人是交流的主要功能。
說故事是交流的形式。
因此,說故事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影響他人。
不僅如此,故事是人們——不單單是小說家廣告業者——影響同伴的主要方式。畢竟酒吧內的人不是在談論重要項目,也不是滑稽的狗和令人失望的男友,他們說的是關於自己的故事。電視裡的記者在說故事、演員將故事表演出來、憤怒的前運動員拚命將格隆考夫斯基的故事添加到已經宛如一齣肥皂劇的新英格蘭職業足球隊。那齣廚師實境秀根本不是烹飪節目,而是主角努力爭取幸福結局的故事,伴隨著節目主持人以各種或合理或下流的手段製造衝突及增加戲劇性。
人類的首要行為即是穿梭過千言萬語,這些隻字片語沒有被統整成PowerPoint 簡報、說明手冊、試算表或是各類清單。我們每天都花費大把時間遊走於各種敘述句中——從孩子們的冷笑話、超市裡的八卦、行銷或宣傳活動,到美國人每天平均花費四小時以上看電視,再到有關我們國家及宗教迷思的小小篇章。
這是因為故事是影響他人思想的唯一有效方式。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找到的最好竭力影響他人的方法,讓我們總能維持順應情勢、能屈能伸的狀態。當故事的龐大益處被導向了促進同理心、體諒、慈善和和平時,著實是件美妙的事。然而說故事的影響魔力同樣也會種下分歧、懷疑和仇恨的種子。你可能有所懷疑,也應該要懷疑才對,畢竟我雖然自稱是學者,但截至目前為止也只講了一個故事。若你讀完這本書後只學到一件事,那麼這件事應該是:千萬別相信說故事的人。
但我們信了,真的情不自禁地信了。
就跟小狗和彩虹一樣,我們一致認同故事是讓人生變得更美好的事情之一,這種本能的、無條件的癡迷正被一種泛文化運動強化,它慶祝著講故事在商業、教育、法律、醫學、自我提升和其他領域中發揮了變革的力量。然而這種根深蒂固的信任賦予了故事某種力量,讓故事變得比理性的論證和確鑿的事實更加難以抵擋。當人們被問到自己的思想行為是否受故事影響時,大多都會說:「還好」。4
諷刺的是,我們自認不受故事影響的自信,正是自己備受影響的原因——儘管對我們來說有時是正面的影響,但往往不盡然如此。
我寫過一本《大腦會說故事》(The Storytelling Animal),主要探討故事是如何讓我們變得更好。這本書重新修訂了前一本書的主題,但更加著重於故事的壞處,尤其是針對整個社會,而非僅僅是個體層面。所以說,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本書最後我會解答這個問題,而現在我將先點出一個這本書不會探討的空想:柏拉圖那著名的觀點,或許能將說故事的人逐出社會、或是逐出任一個我們渴望生活的地方,但是就跟呼吸和睡眠一樣,人類不能沒有故事。因此,整本書的內容,我都會試著用最具影響力的方式——說故事的方式,來說明故事的力量。
角色扮演遊戲
男子今年四十六歲。他身材魁梧、內心驕傲,一個朋友都沒有。他曾經有工作,但已經失業了一段時間。以前的同事們都很喜歡他,他會參加派對和同事的孩子們玩耍。朋友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巴布斯。他從未惹過麻煩,從未傷害別人。當他購買一些重型槍械時,背景調查顯示一切正常。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這名男子不再像從前那麼討人喜歡。事實上,他內心充斥著暗黑思想和衝動。在那個十月的早晨,我想像他和大學生一樣吃了沖泡燕麥和玉米片當早餐;我想像他一邊滑社群媒體的貼文一邊啜飲咖啡,對著某些貼文微笑、對著某些直搖頭。接著,他在自己的帳號上發了一則影響全世界的動態之後,他將包包扔進卡車,開了十五分鐘的車,到了松鼠丘綠樹成蔭、繁榮的匹茲堡社區。
我很好奇開車時他在想些什麼。他害怕死亡嗎?害怕殺戮?他有沒有在最後一刻停下來思考整件事?他是否因為滿腔的正義而熱血沸騰?或者他就和其他駕駛一樣,被匹茲堡隧道內壅塞的交通分散了注意力?
這名男子把車停在生命之樹猶太教堂前,接著逕直走入大門開槍掃射。「所有猶太人都必須死!」他一邊扣下AR-15 步槍和格洛克點三五七手槍的扳機一邊怒吼。
在第一批警察到達現場之前的幾分鐘內,十一位民眾遭到殺害,更多人受傷。在被武器與戰術特警人員射傷後,男子才終於投降。就在警方搶救他的生命之時,嫌犯試圖解釋自己的行為。他要警察明白,自己並不是那種抱持虛無主義、無緣無故闖入學校或商場的瘋狗。若他真的犯了罪,也是為了阻止一起更大樁、更令人髮指的罪行。猶太人正在實質地入侵美國,並以緩慢的速度針對白人進行一場種族滅絕。那晚,我駕車半小時去到松鼠丘參加倉促舉辦的守夜行動,愣愣地從上千名哀悼者身邊走過。我心想:這一切,這些死亡和悲傷,全都導因於一則故事。
故事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古老珍寶之一。它宛如永不腐朽的物件般穿行過歷史的洪流,無論我們如何想方設法消滅它、無論多少證據被提出來反對它,它都蹣跚地克服了阻礙。
故事始於《新約》,接著篇幅越來越長、越來越長,引發一場又一場大屠殺。從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ius)洗手到《錫安長老會紀要》,再到Stormfront.org(白人優越主義網路論壇)發布的宣言,無數版本講述的皆是同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如下:猶太人是歷史上的吸血鬼,憑藉著邪惡的聰慧和貪婪,這些次等人界的超人正在策劃一起為其數千年的陰謀,用以鞏固、增強他們自己的力量並荼毒奴役其他人。若有好人起身擊退猶太人,若我們能掙脫他們加諸在一切美好事物上的束縛,一切終將歸於美好。
這個故事如此熟悉,以致於有人對其荒謬的程度已然麻木。因此,陰謀論者大衛.艾克(David Icke)的論點或許能提供點幫助。他一直以來致力於宣稱我們全是第四維度外星蜥蜴的奴隸,但卻對此毫不知情。我們沒有發現所有美國總統都是外星蜥蜴,因為他們的縞瑪瑙眼珠和滿是鱗片的尾巴都被全息面紗蓋住了。艾克聲稱他自蜥蜴霸主的特殊飲食偏好中找到了人類苦難的根源,蜥蜴以人類的能量為食,苦難對牠們來說是最甜美的氣息。所以說,蜥蜴用戰爭、貧困和疾病折騰人類打造一座悲傷滿溢的河谷,接著牠們就可以用那爬蟲類的細薄舌頭輕輕舔拭所有苦痛。根據民意調查,有一千兩百萬名美國人信以為真。5
現在,讓我們回到上面的段落,改以「猶太人」這個詞取代「外星蜥蜴人」,便會發現這則故事不只引發了生命之樹屠殺事件、更是納粹行動的根源(有人指責艾克為全世界猶太人的陰謀編寫了一則詭秘的寓言。針對這個反猶太主義的指控,艾克發現了更多世界蜥蜴陰謀論風潮抹黑他的證據)。一九三三年納粹掌權,希特勒指派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成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此部門將德國整個講故事的行為納入政府的掌控之下,藉此創造一個全新的國族事實。廣播、紙本、新聞短片、演講,甚至是造謠的耳語,納粹的宣傳員們好像講了很多故事,但實際上卻都是同一則:雅利安騎士在人類最後、最偉大的舞台上擊退猶太惡魔。這個故事簡而有力,如此震撼著大眾,使得虛構的內容成了真實。6
這則故事引發的苦難規模遠遠超過了人類所能理解。不只是大屠殺,反猶太主義也是納粹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理由之一。7
除了有上百萬猶太人喪命,這個故事也釀成了千萬人死於戰爭之中,更引起了無數起肢解與強暴事件、古城慘遭蹂躝,以及無盡的實質與文化財產毀於一旦。一切的一切都是導因於跟大衛.艾克那的蜥蜴妄想一樣愚蠢的邪惡猶太人故事。
現在,因為這則蠢故事而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也包含了生命之樹猶太教堂的單人兇手大屠殺事件。殺手開槍掃射前,在社群媒體發佈了這則惡名昭彰的貼文:「HIAS(希伯來國際援助協會,Hebrew International Aid Society)很喜歡帶入侵者進來殺害我們的同胞。我沒法坐視不管。看清楚了,我要進去了。」
殺手是這樣說的:我不是笨蛋,我知道對著一群無助、大多都是老年人的禮拜者開槍胡亂掃射看起來很不光彩,我知道我簡直像個怪物;但看仔細點,我不是怪物,我是為了殺死怪物而犧牲一切的好人。
14.8 x 21
25 開
前言 千萬別相信說故事的人
第一章 會說故事的人統治世界
第二章 說故事的黑暗藝術
第三章 故事王國的大戰
第四張 故事的通用語法
第五章 故事讓人們分崩離析
第六章 故事會讓現實終結
結語 來自冒險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