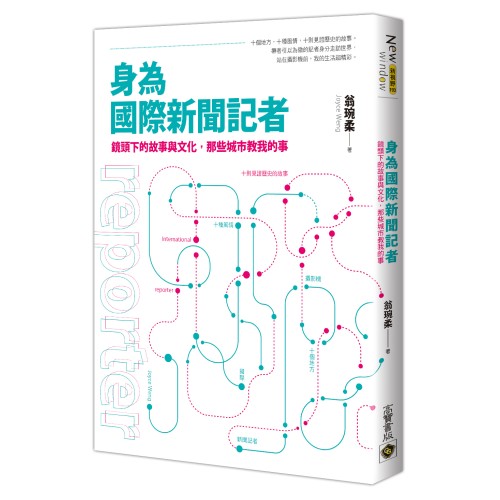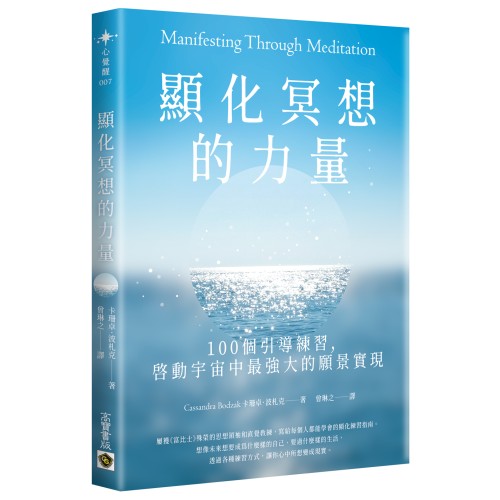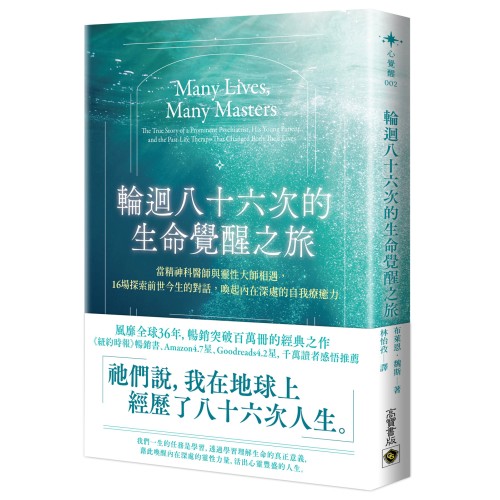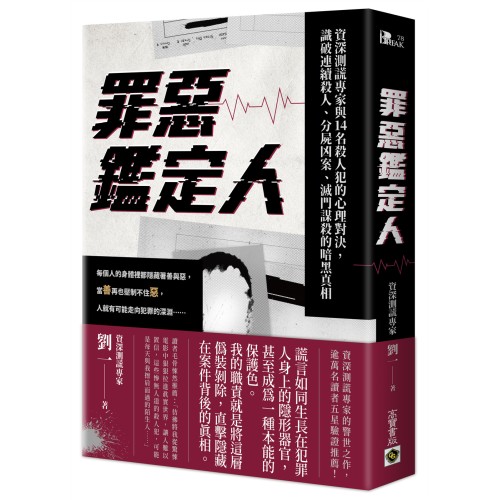- 內容介紹
- 線上試讀
- 商品規格
- 書籍目錄
誰說台灣沒有國際新聞?我們正是分分秒秒在見證歷史,勇於站在世界最前線的一群人。
十個地方,十種風情,十則見證歷史的故事。
帶著引以為傲的記者身分走訪世界,
站在攝影機前,我的生活超精彩。
記者可說是一份吃力不討好、投資報酬率極低的工作,
但如果再問我一次會不會選擇這個職業,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永遠記得最初心中「想站在新聞現場」的渴望。
每位記者都是抱持著想將第一手消息傳達給觀眾的熱忱奮力奔波,身為一名國際新聞記者,表面看來光鮮亮麗、走訪各處,但鏡頭之後的超時工作與輿論批評卻也同時壓得這些歷史最前線的記者們喘不過氣。
「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台灣沒有國際新聞」,這些是針對台灣媒體產業流行的話語。本書以深刻的現場回顧與內在反思打破刻板印象,帶領身為閱聽人的我們一同感受日本災情與感恩並存的時分、南北韓高峰會令人屏息的一刻、馬來西亞威權下的掙扎、俄羅斯戰鬥民族性格的不容小覷,共同體驗與世界大小事並肩前行的悸動。
本書更收錄琬柔於紐約念書深耕、聯合國實習的見聞,期盼自己,亦或是對媒體產業有憧憬的人們,對這份職業有更深刻的見解,讓媒體之路更為寬廣。
不論是跑新聞或是進修,這些異國經驗,都觸發了身為媒體人的快感,只要在國際新聞現場,琬柔就覺得自己的生命好精采,一點都沒有浪費,也能抬頭挺胸地說:「誰說台灣沒有國際新聞?」
★★★專業推薦★★★
資深媒體人/岑永康
壹電視主播/沈泳吟
東森新聞主播/陳瑩
三立新聞主播/張齡予
節目主持人/蔡尚樺
熊本──坍方磚瓦壓不垮的溫暖人心
「日本九州熊本在昨天晚間,發生了規模六.五的強震,最大震度高達七級,當地的益城町成為了重災區,房屋受損情形相當嚴重。」
二○一六年四月十四日晚間,熊本發生了大地震,睡前在手機看到新聞,心想隔天有得忙了,果不其然,因為國際組裡面會日文的人數屬於相對少數,於是我被調到晨班,凌晨五點就抵達辦公室,忙著處理熊本震災新聞,由於災情實在太慘重,長官指示,要我儘快梳化,直接進棚以推播的方式,即時更新熊本災情。在辦公室跟攝影棚之間穿梭,看著NHK 傳來的畫面,熊本城的磚瓦都因為地震而垮了下來,木造民宅更是倒的倒、塌的塌,傳出多名死傷,雖然是透過鏡頭看著這些畫面,景況還是相當震撼,不過身為新聞工作者,只要是在工作期間,其實沒有太多的時間感到心痛或是難過,因為我們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消化大量的訊息,並且傳達給觀眾。舉例來說,像是熊本發生地震的時候,由我一個人負責每一節新聞的即時推播,雖然可能只在電視上現場播報三分鐘,可是我得在上台前掌握最新的災情、找到外電傳來的最新畫面、跟動畫溝通CG 的內容、在公司內部系統打好標題以及給主播的新聞稿頭,這些步驟通通得在五十分鐘內完成,
每個小時都是這樣循環度過。好不容易到了中午,換下套裝,準備下班回家的時候,長官稍來最新的指令:「去熊本吧。」
重大災情發生的時候,就能考驗團隊分工合作的能力,我立刻出發回家收拾行李,長官負責幫我找落腳之處,公司的行政忙著幫我們訂機票,最後當地的飯店因為地震都不接受訂房,我們只能入住市區的Airbnb,台北當天沒有直飛熊本的班機,所以我跟攝影得從台北搭高鐵到高雄小港機場,再前往目的地。
前往熊本的班機上,只有一團不到二十人的旅行團、我跟攝影記者、以及兩個平面記者。服務我們的空少,來來回回走動,看著我們的攝影器材,笑著對我們說:「辛苦了」,又可能因為客人實在太少,他殷勤地問我們要不要喝點調酒,他可以幫我們特調。早上五點就上班的我身體其實很疲累,但是第一次採訪災難新聞,又在人生地不熟的熊本,我們甚至連採訪車都沒有,焦慮的心情讓我沒心情喝酒,更是連閉上眼睛補眠都無法。
抵達熊本的時候已經是當地的晚上,我們叫了計程車趕往重災區益城町,因為地震導致線路毀損,熊本大停電,一路上黑漆漆的一片,沒有商家營業,路燈也比以往微弱,景象跟二○一一年三一一大地震的東京有幾分相似,整個城市一點生氣都沒有。到了益城町,在街頭查看了一下民宅受損的狀況,有許多民宅倒塌、磚瓦掉落,已經不能住人,救難隊就在街上的空地紮營,避難中心已經有許多物資湧入,居民也受到良好照料,簡短採訪、做好即時連線後,我們接近午夜的時候才回到了Airbnb,小小的套房,不是非常乾淨,廁所也相當老舊,讓有點潔癖的我覺得受不了,但這種非常時刻我也不能抱怨,跟長官簡短回報後準備就寢,隔天還要六點就開始連線呢。
眼睛才剛闔上,突然一陣天搖地動,不只前後搖晃,還時不時垂直型震動,
三層樓的房子被搖得嘎嘎作響,睡在榻榻米上的我,張開眼睛,還在思考「發生什麼事」的時候,聽到櫃子倒塌的聲音,櫃子上的電視、飾品全都砸了下來,這時候夜燈啪一聲熄了,連市區的電都停了,我看了看手機,是半夜的一點二十五分,我睜著眼睛思考要不要逃命,起床披了件外套抓著手機,想看看外面的情況,結果一打開門,我的攝影搭檔已經扛著攝影機,在公寓走廊上拍著街上出來避難的居民,冷靜看著我的眼神彷彿是在說:「妳怎麼現在才出來。」
「到街上拍吧。」他對我這麼說。
四月的熊本晚上氣溫很低,所有在街上避難的人都縮著身子,我們在黑暗中隨著人群移動,走了約莫十五分鐘,抵達了附近的大學校區,草地上擠滿了不敢待在家中的居民,他們拿著野餐墊鋪在地上,有些人披著棉被,到了深夜兩三點,所有人都還睡不著,但也沒有人說話,整個戶外空間只聽得到風吹的聲音,還有時不時傳來的餘震,居民的臉上寫著恐懼跟不安。
我們回到住宿的地方打算稍作休息,因為明天還有硬仗要打,但是幾乎每半小時就會有一次餘震,我整夜都無法入睡,天亮了,真正的考驗才來了。原來,半夜發生的這場地震,規模高達七.三,比前一次的地震規模還大,日本氣象廳定調,四月十六日一點二十五分發生的這場地震是「主震」,而兩天前發生的天搖地動只是「前震」,而因為這場半夜發生的主震,益城町傳出更多災情,更多的房子垮了、死傷人數也往上增加。
我們焦急地想從熊本市區趕到重災區益城町,這才發現叫!不!到!計!程!車!
原來因為地震震壞了聯外道路,車子進不來,汽油儲存量也不夠,整個熊本的公車停駛,只剩下七輛計程車營運,但是主要的用途都拿來協助有需要的災民移動,行程爆滿無法為我們服務,警察幫我們寫下了所有他知道的計程車車行,打遍電話都沒有車,公司裡的長官跟編輯們正在焦急地問我們下一則連線什麼時候可以連?什麼時候可以前進現場?什麼時候有畫面?問題是我們連災區都進不去啊!
國際組沒有固定的攝影搭檔,每次出國就像是在抽彩券一樣,搭檔的好壞決定了一切,這次跟我去熊本的攝影是一位經驗十足的大哥,國際採訪經驗豐富,他在此刻輕聲說了一句:「沒車的話我們走去吧。」我們的攝影器材將近二十公斤,從市區走到益城町少說也要兩、三個小時,用走的?!
我雖然百般不願,但是走路進災區似乎是唯一方法,於是我們真的提起行囊準備徒步進災區,好險走不到一小時,Airbnb 的主人答應我的請求,願意開車載我們協助採訪行程。
終於,趕到益城町之後,我們發現我們到達第一晚看到的、本來只是半倒的平房都垮了下來,街上的房子破損的更嚴重了,許多停在家裡前院的車子都被壓壞,居民全都集中在避難所,就算在住宅區看到人影,也只是居民趁著白天的時候回家拿取重要財物,整個城鎮的景象只能用淒慘來形容。這種時刻的採訪,真的相當令人感到心痛,心裡真的不想打擾災民、或是喚起他們慘痛的回憶,可是身為新聞工作者,了解事件發生當時的情形,是我們的職責,把當地狀況傳遞給觀眾,更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我們採訪到一個家庭,走進他們殘破不堪的家,掉落在地上的時鐘就停在前震發生的時間,整個屋頂半垮,停水、停電、地板上都是磚瓦砸落的碎片,看著眼前不知道從何整理起的景象,女主人卻很堅強地告訴我們,他們一定會回到這個家、一定會致力於重建。
「是的,記者現在所在的地點就是熊本的益城町……」在每一個災情慘重的地方,我們都會抓緊時間趕快連線,但幾乎每次的連線,都會被手機的地震警報發出的巨響給打斷,因為在地震發生隔天,熊本還是餘震不斷,讓我們得在搖晃中採訪、連線。就這樣,我們一整天穿梭在重災區跟避難中心,請民宿主人開車帶我們造訪所有災情嚴重的地方,公司要求我們一小時要傳回一次連線,我們幾乎是連線完就得趕往下個採訪地點,沒有任何的時間,更沒有心情休息。到了傍晚,我發現喉嚨已經有點發不出聲音,原來我們從抵達熊本開始,就沒有進食過,由於便利商店都沒有營業,所以也沒有水,路邊的自動販賣機只剩下氣泡飲料,別無選擇之下只好靠著喝可樂來補充水分。到了深夜,手機傳來家人的訊息,要我小心,原來他們看到我站在阿蘇山區因為地震坍方的斷崖連線,嚇得心臟差點跳出來,那是一條山路,馬路因為地震硬生生被拆成兩半,我的攝影想辦法爬上
馬路的對面,用遠景的方式呈現出整個道路崩塌的樣子,我就站在殘破的馬路上連線,再往前一步就是斷崖,連線前還碰上了餘震,但是當時我手上握著手機,查著日本官方給出的最新訊息,準備連線內容,心中一點害怕或危險的感覺都沒有,但是這樣的畫面看在家人朋友眼中,讓他們擔心不已,我現在再看一次,也著實感到怵目驚心。
在災區採訪第三天,災區的一切慢慢有了秩序,有些地方的電力慢慢修復了,走進避難中心,雖然空氣中瀰漫著不安,卻還是對日本人的有條不紊感到相當佩服,自衛隊在外面準備餐點,居民耐心排隊,沒有爭先恐後的情況出現。避難中心內,有各大電信公司提供的充電場所,有傳言版提供災民之間的訊息聯絡,醫護人員進駐,物資也相當齊全,災民看似受到妥善照料,只是熊本餘震不斷,有許多居民不敢待在室內,選擇睡在車子裡面,有些人則開始出現機艙症候群的症狀。所幸,整天下來接受我們採訪的人,都很平靜地看待眼前的狀態,印象最深的是,在一個避難中心,採訪了一個正在排隊領取物資的大叔,他一聽到我們是台灣來的媒體,便低頭跟我說:「請你們一定要跟台灣的觀眾說謝謝,謝謝你們在三一一大地震的時候捐了這麼多錢給日本。」
在這次的採訪,我真的看到了很多人性正面的地方,除了在這種非常時刻還記得跟台灣說謝謝的災民以外,所有我接觸到的熊本人,面對這場災難,沒有大哭大鬧、沒有貪婪搶奪,那樣平靜的氣氛,讓我至今都相當難忘。當然還得感謝四天下來跟我相依為命的攝影搭檔,採訪的前三天,我們真的一口食物都沒有吃下肚,但是他不曾開口抱怨,住宿的地方整整四天都停水,我們在第三天終於買到礦泉水的時候,他還把他的份分給我,給我卸妝洗頭洗臉(是的,在災區採訪的四天內我到了第三天才有水電梳洗),更要謝謝熊本,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也希望把最大的祝福,獻給熊本。
新加坡──見證台灣年輕人的堅毅
我大學畢業那年,碰上雷曼兄弟倒閉的金融風暴,畢業近乎是等於失業,政府祭出22k 方案補助,希望能促進企業聘雇剛出社會的新鮮人,沒想到許多企業一毛都不肯多加,讓很多大學畢業生剛出社會領到的薪水就是不多不少的兩萬兩千元,當時跟我同一屆畢業的朋友們,幸運一點的可以找到起薪兩萬八的工作,但是絕大多數的人,月薪都在兩萬五上下。
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澳門的賭場開始來台灣徵才,號稱月收入可以是台灣的三到四倍,新加坡也到台灣誠徵各路好手,雖然大多數的職缺也是集中在服務業,但是也有部分科技、醫護、文創產業的職缺。
在我小時候,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給我的印象是威權統治盛行,老師用新加坡「隨地吐口香糖就會被鞭刑」的故事對我們諄諄教誨。但是隨著新加坡的發展,近年來新加坡的國際形象已經轉變成高品質、說雙語、經濟發展有前景的地方。二○一三年,麵包師父吳寶春決定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念EMBA 的事情吵得沸沸揚揚,也不難看出新加坡已經把「人才」視為最大資源,不僅企業廣為接納國際人才,更透過教育向下扎根,想吸引一流人才到新加坡發展。
漸漸地,網路上類似「我二十五歲,在新加坡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文章也越來越多,但即使這樣,小學時老師們半開玩笑、半憂心地對我們說:「不好好念書,以後就只能出國賺錢當台勞。」這些話仍言猶在耳,似乎也成了梗在我心中的一根刺,對新加坡的徵才廣告總是充滿疑問,心中也曾經偷偷覺得,雖然很多人號稱到新加坡擔任服務業,薪水可以拿到台灣的三倍,但是新加坡物價高、再加上房租,這撈金夢真的這麼容易達成嗎?
而國際新聞記者這個身分,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藉由工作,帶著我走出世界,用自己的雙眼去見證,並且解開我心中的疑惑。
二○一六年十月,我們收到一個面膜品牌的採訪邀約,一個年紀跟我相仿的台灣女生艾兒莎(Elsa),放棄了自己22K 的薪水,隻身一人到新加坡闖蕩,就這樣眼界被打開之後,在東南亞找到了商機,開啟電商之路,在網路上販售用中藥材萃取的面膜,因為身處國際人才匯集的新加坡,投資者對於任何新奇的點子都抱持開放態度,也讓她迅速集資創立了人才招募公司。
艾兒莎的故事,聽起來非常傳奇,也的確在網路上吸引了數十萬粉絲,有許多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被她的故事激勵,決定不要被困在台灣,要勇敢走出去為自己尋找更美好的未來。
如果把這些艾兒莎告訴我的故事,原封不動地報導出去,的確,應該會吸引不少觀眾的眼球,但是作為一個心中對於「赴星打工」抱有存疑的記者,我實在不想就這樣變成幫新加坡的就業市場拉走更多台灣人才的推手。於是我想要跟在新加坡做服務業的台灣年輕人聊聊,還想走入他們住的地方,親眼看看他們真實的生活。
艾兒莎介紹了她的朋友曼文(Amanda)給我認識,當時歲的曼文本來在台灣從事服務業,薪水只有兩萬四,後來到新加坡的精品店上班,薪水翻漲了三倍。這聽在台灣觀眾的眼裡可能很多,問題是新加坡以高物價聞名,這薪資在當地根本就不算高,走進曼文的家,她跟朋友分租了公寓裡的一間雅房,小小的房間裡擺了兩張單人床後連桌椅都擺不下,衛浴還要跟所有室友共用,即使這樣分攤下來房租還要大約一萬五台幣,外食、娛樂享受所費不貲,所以曼文剛到新加坡的時候幾乎三餐都自己煮,要很節省一個月才能存下兩萬台幣的存款。也就是說,如果不小心失手購物、或是娛樂行程變多、甚至是回趟台灣,變成月光族的可能性也不小。
當時的我住在家裡,每個月扣掉吃喝玩樂之後,要存下兩萬塊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難,所以看到曼文的房間那麼小,甚至一點私人空間都沒有,我不禁質疑:「這樣不辛苦嗎?真的值得嗎?」曼文想都沒想就說:「辛苦啊!」正當我想接下去問:「那為什麼要跑來這裡吃苦?留在台灣生活品質可能還好一些。」的時候,她用堅定的表情看著我:「可是,這都是成長的一部分。」當時的我有點愣住了,我受到家庭保護,不需要負擔房租,躲在自己的舒適圈,用自己的眼光質疑這批受夠台灣低薪環境的年輕人,對於這樣的自己深切反省。在新加坡採訪的時候,跟許多投資者跟企業家聊天,所有人都對台灣人才讚不絕口,英文能力強、適應力佳、工作起來又很拚命,讓我不禁疑惑,既然這些人這麼好,為什麼台北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跟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台灣人聊過之後,也才慢慢理解到,他們要的或許不是這一時的薪水,更多人求的是經驗,或是跳往東南亞其他國家發展的機會。用「台勞」的框架圈住他們,真的有點不公平。
我們這代的台灣人,從小就被五六年級生定型為草莓族,一壓就爛、吃不了苦,可是這群人,卻拿出了自己最堅強的韌性,在新加坡過著我眼中的「苦日子」,一切都是希望能在這個國際化的社會,找到更美好開闊的未來。
透過採訪的過程,我的確被說服了,也對於「新加坡的台勞」徹底改觀,但是在製作新聞的時候,我依然不想要大力宣傳在新加坡上班的好處,因為我相信,台灣人,只要夠優秀,在哪裡都會有機會。所以我把曼文的故事寫進稿子,但是也把新加坡的租金、物價製作成表格,提供客觀數據平衡報導,這一切值不值得,全都交給觀眾來評斷。
很多人在批評新聞媒體的時候,都會說記者不應該有立場,但是身為新聞從業人員,我認為,只寫事實的,那叫訊息,帶著觀點跟分析的,才是有深度的新聞報導。這次在新加坡的旅程,雖然只佔有我新聞生涯的短短四天,但是卻讓我深深感受到台灣年輕人的堅毅、競爭力,更重要的是,我學到雖然新聞一直容許有立場,但是在有自己的立場、觀點的狀況下,敞開心胸去傾聽受訪者的聲音,把最真實的情況呈現給觀眾,才是記者最應該做的工作。
14.8*21*1.3
25 開
推薦序
她,新聞從業路上的夥伴、偶像
身為記者,終其職涯,我們就是在等待「新聞魂」燃燒的那一刻!
打開關於異國文化的眼界,走進新聞幕前幕後
堅韌與柔軟並存,帶回無數新聞價值
第一章 身為一名新聞工作者
為什麼想當記者?
我的生活很「國際化」
雞生蛋,蛋生雞
台灣的酸民文化
第二章 我的現場直擊與文化觀察
曼谷 探索「人味」故事,我的新聞夢想基石
大阪 鴻夏戀
熊本 坍方磚瓦下壓不垮的溫暖人心
東京 與最有溫度的機器人做朋友
新加坡 見證台灣年輕人的堅毅
吉隆坡 拒絕成為威權體制下的犧牲者
首爾 朴槿惠罷免事件
首爾 歷史最前線:南北韓高峰會現場
莫斯科 漸入佳境的北國記行
[同場加映]
台東出任務――尼伯特颱風災情連線
第三章 記者之眼的紐約臥底觀察
記者之眼的紐約臥底觀察
記者身分在紐約
第四章 聯合國實習筆記
我在聯合國做什麼?
台灣需要的不只是國際新聞
在聯合國工作的台灣人
後記


-500x500.jpg)